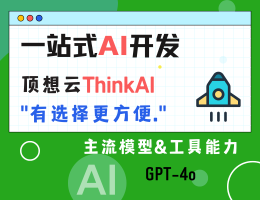小當不可避免的消沉了一段時間,但所謂人心是不待風吹而自落的花,世間流言也是如此,時間過去很久,久到村子里的人,包括小當都忘記了小當挨打的那次,可是有首詩,縈繞在小當心頭,更先縈繞的,是村尾的電線桿,沒錯,詩人刻的。
  看著這根筆直的電線桿,小當吐了口唾沫,提起了半口鍘刀,拖著往村尾的孤宅走去,是的,在古代,無數人逝去后活在詩歌里:但使龍城飛將在,不教胡馬度陰山。如今小當也有了活在詩作里的機會,可是怎么看,怎么都是“人從宋后無名檜,我到墳前愧姓秦”這類。鍘刀拖在地上哧哧的響,走到一半,小當心頭一顫:“不對,詩人這個東西,住在歷史上是神仙,住在你樓上,他就是個瘋子。那么,萬一不敵被反殺,瘋子豈不是不犯法?”小當長吁一口氣,還是應當先行拜會一下這位當代詩人。
  抱著懷柔政策的小當,手里換了樣東西:一跟葦草,見詩人當然不能帶俗世的東西,否則一見面就輸了,草中自有深意:矮紙斜行閑作草,本當就是想問你是不是閑的!一路無語,小當行至其西門,拂袖奪門而進,缺見一人披發行吟于澤畔,顏色憔悴,形容枯槁,雙眼有神而游離,手擎木杖,年紀六十有余,此老猛抬頭:“來者可是,諸葛孔明?”
  小當:(●′?`●)。
  老詩人:“咦,你,,竟也尚存于世間。”
  小當:“死生非吾之愿,冥冥天定。”
  老詩人:“哈哈哈,小生有趣,請回吧!”
  小當:(●′?`●)。
  老詩人:“等等,你這手持一草而來,可是罵我?”
  小當:“這株葦草,是我在一根電線桿下拾得,當今世界,熙熙攘攘,皆為利往,此草也算是見證了這個春秋。根據這根草的見解,從來都是有人在電線桿上貼小廣告,未想到近來竟然有人會在上面刻詩,今日我讓它引路,所以尋到這里,會會這路邊刻字之徒!”
  老詩人:“哈哈哈,伶牙俐齒,草木皆兵,有趣,請回吧。”
  小當似乎懂了,一挽手,搖搖頭,似有幾分寬恕的說道:“人們期盼的,僅僅像是追逐著漁網的海鳥一樣罷了,總以為自己翅膀上折射著自由的光。”
  說完,著重看了一眼柴門前的婆婆丁,嘴角微揚,轉而就要離去。
  老詩人一驚,思維狂轉:這小子這句話好陰,貌似毫無根據,可是又像是極富哲理。我要是裝作沒懂,這廝一定借機諷刺我,以后我見到他都抬不起頭來,我要是裝作懂了,可是我丫的真沒懂......麻蛋,這我絕對不能接。
  老詩人輕咳一聲,說道:“哈哈哈,你想看看我的詩嗎,我認為你完全有資格代替我在這里作詩。”
  兩人雙雙落座,老詩人拿出一張草紙,說:“今日遇此了了少年,有幸成詩,快哉!”說完提筆疾書,成詩曰:
>尬詩第一首<br>
三十歲還未走形的女人
能否再給她一次青春
用這七年的煙酒
換一下耳畔的笑容
換一下和風
換一下告別的手
小當打了個哈欠,問道:“你見過這樣的女人么?”,老詩人一愣,摸了摸木杖,答道:“這要看你對走形的定義了,小子,你經常做的夢是什么?”小當:“emmm~,兩排樹木的鄉間小道,有一車寬,被人追殺落荒而逃的我,不知走了多遠多久,就在路邊,撥開灌木,遇見一個大湖,一座木屋,奇幻的光影透過四周茂密的樹木映入我的眼中......”“后來呢?”“后來我掉進湖里,每每這時我就醒了,沒有一次例外,為什么掉進水里也不記得,也曾在夢里警告自己不要掉進去,卻沒成功過。”“玄妙~”老詩人瞇起眼睛,似乎在細細品味這個夢,又繼續說道:“這就是你每次尿床的借口么?”小當立刻叫道:“什么啊,我可是在10歲以后,了解了什么是愁之后才夢到的呀!”
老詩人似乎在順著話題尬聊,繼續問道:“那你現在愁些什么?”小當眨了眨眼,說道:“現在嘛,正是農閑時節,等到九十月,我將變成拉磨的驢,秋收到農閑,農閑到春種,再到農閑到秋收,一環一環,就像磨盤拉了一圈一圈,像那游戲開了一局一局,我在愁什么,大概在愁一眼一生吧。”
老詩人呆了呆,冒出一句:“不如跳舞”小當:“啊?”老詩人緩過神來:“今夜子時我會踏馬江湖,千里訪友,你若是想錯過今年秋收,就帶好你的行李,我會在村外十里倚馬觀星,有緣再見。”講完老詩人起身進了屋子,留下莫名其妙的小當,小當隨即大喊:“哪個方向啊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