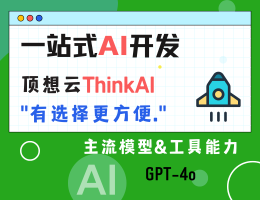沿三佛齊水道東渡,再向北,一路無事到了占城國。占城以稻米出名,怯綠連號入港購買了二十石大米。加足淡水后重新上路。
瑪魯問鐵木真:“你們蒙古人不是不吃五谷、專食牛羊的嗎?”
鐵木真笑著說:“誰說的?當年忽必烈汗曾經對高麗使者說:‘借道高麗,日本朝發夕至。舟中載米,海中捕魚而食之,則豈不可行乎?’可見蒙古軍隊也是吃大米的。不僅食米,還吃海魚。”
“這樣一顆一顆的東西可怎么吃啊?一定會在嘴里跑來跑去。”
“你可以捏住它們,不讓它跑。”鐵木真笑道。
“該死的鐵木真,當我是傻瓜呢”瑪魯拉著馬明進了船上廚房,大米已經煮熟了。她用煮飯勺舀起一塊,再用叉子撥來撥去,撥得散亂在盤中,最后一咬牙說:“就當它是魚籽醬吧!”
馬明見她把胡椒、鹽紛紛撒到米飯上,笑道:“那樣不好吃的。我們在麻林地的時候不那么吃。”
“那你們怎么吃啊?”
“把米嵌在羊排骨上,燒熟了吃。”
“我情愿像你說的那么吃”
“小姐,你不小心把米飯撥到地上了。”
瑪魯連忙蹲下去撿。馬明也陪她蹲在地上,小聲說:“喂,你不用這么害怕的,這不算犯錯。你和我都不會受罰。”
“可是,這是鐵木真花錢買的呀。”瑪魯可憐巴巴地說。
“他的就是你的嘛。”
“你還在提這件事!”
馬明湊近瑪魯,低聲說:“實際上,我從來沒有忘記那件事!我還知道,你到廚房里來嘗稻米,也是為了以后能跟他一起吃飯。”
“你說什么呀!”瑪魯小聲嘀咕著。
過了一會兒,她不知不覺地又自語起來,或者說不是自語:“你說,他一點表示都沒有,我總不能死皮賴臉地纏上去吧?”
“他是誰呀?”
馬明見瑪魯面露不悅之色,趕忙幫她收拾了地面的米飯,又把地板擦得干干凈凈。然后,跟瑪魯一起端著飯走向船長室。
“拔都病了。”船上的蒙古大夫對鐵木真說,“打擺子,又吐又瀉,渾身出冷汗。”
“是么?”鐵木真放輕步履走進他和拔都共用的臥艙——從出海時起他就跟這個老管家共居一室了。
拔都的眼神已經有些渙散,他欠起身來握著鐵木真的手說:“少爺,我許是伺候不了你啦。”
“你說什么呢!”鐵木真對老頭的悲觀嗤之以鼻,“一場小病,我要你活下去!我的兒子,我兒子的兒子也要你伺候。”他把老頭按回到枕頭上,“長生天保佑你!”
“少爺!”拔都神秘地壓低了聲音,“我不是生病,我是中毒啦!”
“中毒?”
拔都說:“沒錯,船上一定有人下毒!我自己有感覺的,像老獵狗一樣靈。我知道這不是病!”
對老管家,鐵木真是從小就信任的。他摸摸拔都的腦門,說:“你好好休息,我一定查出來是誰在下毒。”
不要說查,第二天,鐵木真自己也“中毒”了,還包括瑪魯和馬明,癥狀跟拔都一樣。都是驟然間上吐下瀉,忽寒忽熱,遍體汗出如漿。為了方便照顧他們,醫生安排這四個人住在一起。
鐵木真自己雖然也受著折磨,卻斜坐在床上,探身摸著瑪魯的腦門說:“老天,不會是疫病吧?”
瑪魯連聲叫苦:“啊喲,好難受啊,鐵木真你別走,你一走我就死了。你仔細摸摸我的頭”可是,她卻在笑。
馬明較為清醒,他輕聲說:“不會是疫病,因為甲板上的水手們沒有一個得病的。”
鐵木真點了點頭:“你說得對。拔都說得對——這不是病,這是中毒。”
馬明呻吟道:“只有只有我們在船長室里吃飯的人,才才得了這個病!有人想害船長。”
鐵木真笑道:“不會,這艘船上每個人都不會害我。包括所有的水手。”他瞪了瑪魯一眼,“也包括你!”
瑪魯嘻嘻笑道:“多謝大汗!”
馬明忽然說:“我好難受!喘不過氣來!到到甲板上去吹吹風”
“病情有變化?”鐵木真擔憂地拉了一下床頭的繩子,這是他們生病之后由醫生給安裝的。繩子另一端系著一枚銅鈴。
立刻就有兩名水手沖進來。鐵木真說:“扶馬明上甲板。還有我。”水手們一人伺候一個,把他和馬明扶起來,走出了船長室。
“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說?”在甲板上,鐵木真問馬明。
“您真聰明,”馬明笑著說,“我想告訴您,我猜到了是誰下的毒。”
“是誰?不會是瑪魯吧?”鐵木真眼里露出恐懼之色。
馬明遺憾地說:“我想告訴您正是她。三天前,她進廚房去嘗飯,我看見她把煮熟的米飯舀來舀去的。她是從來不進廚房的人,怎么會突然想起去舀飯呢?”
鐵木真想了想,笑著說:“不會是她!她難道連自己也一起毒嗎?”
“船長,”馬明說,“她是可以裝作中毒的呀!”
鐵木真出了一陣冷汗。馬明說:“船長,如果你想證明,我們就跟瑪魯小姐分開,不吃她端來的飯,也不喝她拿的水。如果癥侯變 輕了,那就說明她有問題。”
鐵木真微微搖頭:“不好,這樣很傷她的心。”
馬明深深地望了鐵木真一眼,然后說:“好吧,把我和你們分開,如果我好了,就是瑪魯小姐有問題。”
“就這么辦吧。”鐵木真嘆了口氣。
從當天起,馬明就不在船長室吃飯了,鐵木真解釋說,因為他信回教,飲食與大家不一樣,而且每天都要三次面向麥加做禮拜,所以自動請求分開。果然如馬明所說,他的病一日好一日。
鐵木真、拔都和瑪魯的癥狀卻時有反復。通常是每隔兩三天就嚴重一次,這時候,拔都已經開始猜疑瑪魯,連看她的眼神都與從前不一樣了。鐵木真仍然不動聲色。直到發生了又一次海戰。
海戰發生的時候,怯綠連號已經開近了萬生石塘嶼,而船上的統帥層人物全部躺在病床上。連一向強健的鐵木真也是坐起來就頭暈目眩,胸中仿佛有個起伏的大海。瑪魯更是花容慘淡,兩頰原有的玫瑰色早已凋謝,藍眼睛也黯然無光了。拔都年紀大,情況最嚴重,他躺在那里連一根手指都無法動彈,整天陷在昏睡之中。
就在這種情況下,某天上午,鐵木真躺在床上聽見外面在喊:“有敵人!”
他拉了一下床頭的繩子,一個水手跑進來。鐵木真問:“敵人在哪里?”不愧是成吉思汗的后代,遇到敵人,精神就振作起來。
水手說:“在左前方大約五鏈遠,有幾艘船在打仗。不知道是不是敵人”
“扶我上船頭。”
“可是您”
“扶我出去!”
鐵木真靠水手扶持,站上了船頭。他發現瑪魯也跟了出來。
“我害怕拔都的眼睛,”瑪魯笑著說,“單獨跟他在一起,他會殺了我的。”鐵木真一笑。
“命令所有人全副武裝。”他對旁邊的大副薩里木說,“大炮裝彈藥,床弩張弦。”在印度洋上時,馬明已經幫助他按照宋代遺制,造出了十張床弩。牛筋弩弦粗如繩索,以輪軸絞緊,巨斧般的箭頭安在弩槽上,寒光閃閃。這艘怯綠連號在總體戰斗力上已經升級了。
生病之后鐵木真的視力有點變差。他兩手遮在眼睛上方,努力分辨著前面戰斗的幾艘船。瑪魯說:“你想看它們是哪國的船嗎?”
“不,我只想看出它們是哪種戰艦,有什么弱點。”
瑪魯還是告訴他:“其中有兩艘是黃金同盟屬下的海盜船。另外兩艘明顯是東方海盜船——桅桿上飄著日本藩國的旗子。還有一艘,我就不認識了。”
這時距離尚遠,怯綠連號的帆鼓滿了風,撞角高揚,向戰場駛去。鐵木真看見了“同盟”的海盜船上飄揚的黑色兀鷹旗幟,說:“那是蒙古人!同盟里怎么會有蒙古人呢?”
“鷹旗海盜是同盟下屬,他們就用這種旗子。”瑪魯解釋說。
馬明跑過來,大聲喊道:“那是大明的戰船!船長,他們在以一敵四!您快下令過去助戰吧!”
“幫助姓朱的么?”鐵木真冷淡地側過了頭。他的打算是過去幫那些掛兀鷹旗幟的海盜。另外三艘不管是什么船,一律擊沉。怯綠連號靠近了戰場,鐵木真下令:“大炮準備發射!”
馬明聲嘶力竭地喊道:“要幫中國船啊!”鐵木真冷冷一笑,忽然隨著船身一晃,他倒在了甲板上。
兩個水手把鐵木真和瑪魯扶進臥艙。在這種隨浪顛簸而且還頻頻開炮的時候,真不適合躺在床上休息。瑪魯掙扎著坐起來,為鐵木真擦去額頭的冷汗。鐵木真說:“那兩艘海盜船你了解嗎?”
瑪魯低下了頭。鐵木真拉住她的手,柔聲說:“我不該問你。這是讓你背叛同盟。”
“我已經背叛過一次了。”瑪魯說,“那兩艘船都是快速戰船,跟古代腓尼基和希臘的戰艦一樣,是有帆和槳作雙重動力的。兩層槳座共有二百名劃手,撞角非常堅硬,每艘船上安裝有十門炮。”
鐵木真說:“當年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伊,就是用這種船在三個星期里橫渡了愛琴海。”
瑪魯一笑:“你讀了很多書啊。不過,希臘的戰船比這種船要小得多,也沒有炮。”
船身一震,開炮了。鐵木真分辨著炮聲的方位,說:“這是第四號大炮,打得不錯,炮口角度很好。裝藥多了一點,這肯定是那個性急的薩里木干的。他明明是大副,卻要自己去開炮。”“那個薩里木”作為大副有個很大的缺點,就是他喜歡事必躬親。鐵木真曾經對他說過:“你要是不改這個毛病,就一輩子當不了船長,最多是個炮手而已。”他還是改不了,每當有戰斗的時候,他總是放棄指揮而去開炮。
“喀啦”一聲巨響,破碎的木板紛紛射進艙來,還帶有一截鐵鏈子。
瑪魯用身子略微擋在鐵木真前面,說:“這是同盟海盜船的葡萄彈,專門用來截斷敵船桅桿的。打得不準,沒打中。”
鐵木真拉著瑪魯的手:“你坐到床這邊來,坐在地板上。”瑪魯笑著說:“你能這么關心我,我就算為你擋一炮也值得了。”生死關頭,兩人都發現了對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。拔都躺在床上嘶嘶喘氣,哼了一聲。
鐵木真忽然醒悟:“我們這是在跟誰打?為什么同盟的海盜船要向我們發炮呢?”他連忙拉動了床頭的繩子,對跑進來的水手說:“是誰在指揮?”
“是那個在非洲上船的先生,船長!”
“胡鬧!”鐵木真用力撐著床要站起來,“薩里木竟然肯聽他的嗎?”瑪魯鉆到他的臂下,把他撐了起來:“這不奇怪,薩里木肯定又迷著開炮去了。”
“扶我上甲板!”鐵木真把臉側到一邊,免得碰到瑪魯的臉頰,但感覺到她正用嬌小的肩膀支撐自己的全部體重,又聞到她身上一陣陣的脂粉甜香,不由得略覺尷尬。
鐵木真離開臥艙前,從壁上摘下了自己的彎刀。瑪魯臉色一變:“你可不要殺人啊。”
鐵木真笑著說:“怎么啦?你怕我殺馬明嗎?”
瑪魯仰臉瞧著他,小聲說:“我不要你殺人”
鐵木真一笑,把刀掛好在原處。瑪魯雖然自己還步履維艱,卻勉力扶住鐵木真,一步步地走了出去。
甲板上水手們都在跑動,顯然因為沒有稱職的指揮官而心里無底。看見鐵木真,他們都歡呼起來。混亂的局面立時穩定了,鐵木真幾乎是僅憑他的身影就左右了戰局。瑪魯臉上容光煥發,架著這年輕的船長,在他耳邊說:“他們在贊頌你!你是他們的英雄!”
鐵木真招招手,薩里木跑過來。鐵木真說:“把馬明關起來!”
“他已經受傷了,腦袋被炮彈砸了一個洞。”瑪魯低聲驚呼了一聲。大副又說:“船長,還關他嗎?”
“我要關你。因為你不夠堅定,作為全船的代理指揮官,隨便聽從他的意見。現在把二副叫過來,你自己去禁閉艙里反省一下。”
薩里木行了個粗野的禮走了。沒多久,二副跑過來。鐵木真讓瑪魯扶著自己,跟二副一起去看馬明。馬明頭上纏著浸血的布帶,半爬在甲板一角,昏沉沉地還在喊叫:“打!射擊射擊倭寇啊”鐵木真抓住他的胳膊,讓他躺下了。
“大明的戰船呢?”馬明暫時清醒過來,睜大眼睛問。二副望著鐵木真,微微搖了搖頭——瘦削的馬明這時已經是回光返照了。
鐵木真蹲在馬明身邊,低聲安慰他說:“你放心吧。大明的戰船還在,敵人被打敗了。”
馬明臉上露出了微笑。他游目四顧,看見瑪魯,向她伸出手去。瑪魯含淚握住了他那只血跡斑斑的瘦手。
“我向船長告發了你說你下毒對不起!”
瑪魯嗚的一聲哭出來:“馬明,你不要死。我不要你死!”
鐵木真摟住瑪魯的肩膀,對她說:“跟馬明告別吧。”
馬明臨死前,灰暗的臉上顯出一點光彩,他似笑非笑地說:“時候到了安拉在召喚我呢。現在我知道死后應該埋葬在哪兒。我要請你們把我葬回中華。我們家在麻林地已經生活了三代,到我這一代,終于終于回家了。家啊”
瑪魯使勁握著馬明的手:“好,好,我答應你!你的祖墳在哪里?你的老家呢?我一定把你葬回去!”
馬明淡淡地一笑:“無所謂。我已經忘記了只要埋在中國土地上,就是回歸故土了。”他抬眼望著鐵木真,“船長,這里已經是萬生石塘嶼了。我死在這兒,就在附近的海上找座小島,把我埋了吧。我也算了卻了爺爺的一樁心愿,雖說沉船的地方,我不能再帶你們去找了”
瑪魯哭著說:“你不能死。你還得回中國呢!”她仿佛覺得,馬明只要現在能挺住,就可以永遠活下去似的。
“這兒已經是中國了。”馬明微笑著說,“中國的海,跟中國的土地是一樣的。何況還是鄭和將軍航行過的海。我能埋在這里,很高興!” ?
瑪魯淚流滿面:“馬明!你不信基督,可怎么辦啊?隨船的只有薩滿,沒有阿訇”
馬明看了看周圍的人,沒有一個穆斯林,他遺憾地嘆了口氣,低聲念道:“偉哉上帝,惟此一帝謹作此證!”他的眼睛望著天空,竟是死不瞑目。
瑪魯伸出一只手替馬明合了眼睛,淚眼婆娑望著鐵木真:“馬明死了!”
“是的,他死了。”鐵木真拍撫著瑪魯的背,“他是你的好朋友,所以,他也不愿意看到你哭的。別哭了。”
瑪魯問二副:“是哪艘船開的炮打中了馬明?”
“一艘日本船,我也記不清是哪一條了”
瑪魯咬著牙說:“馬明,你靈魂還沒飛遠,在升天堂之前,看著我們給你報仇!”她從懷里摸出一個小鐵盒,打開盒子,里面有幾粒綠色丸藥,她遞給鐵木真一顆:“這是解藥,我們一起吃了吧!怯綠連號需要指揮官。”說完她自己先吞了一顆,“你中的毒比較重,要吃兩顆。”
鐵木真皺著眉說:“還真是你下的毒嗎?我本來不信呢。”他拿起一粒藥丸來吃了下去。這解藥見效奇快,剛剛入腹,鐵木真立刻就心智清明、四肢生力了。瑪魯卻執意要他再拿一顆放在身上,以備萬一二次毒發之用。他讓瑪魯留在艙里,但瑪魯不愿意:“我要看著你把敵人的船打沉!”她只讓二副替她把解藥拿給臥艙里的拔都。
倭寇的戰船上飄著黑色滾白邊的旗子,鐵木真在甲板上叫道:“大家注意,接舷戰的時候要使出我教給你們的戰斗隊形!陸戰隊,各自拿出分派好的武器來!炮手繼續射擊!”
多名大漢各持兵器,排列在左舷,船舷下的帶鉤踏板也準備好了。怯綠連號現在是正對敵人射擊,鐵木真因為拿不準鷹旗海盜是不是蒙古人,所以只讓炮手們射擊倭寇的船。對方也在還擊,但由于視目標比較小,炮彈紛紛落在海里。而怯綠連號上的炮手準確率比較高,已經把一艘敵船打中了,它正在海面上旋轉。那兩艘鷹旗海盜船則悄然撤出了戰場,似乎是不愿與過分英勇的對手為敵,以免雙鋒俱摧。瑪魯大聲歡呼。
忽然,了望手叫道:“敵人派出小艇了!”
鐵木真遠遠一望,果然見倭寇的船旁開出幾艘小艇,由槳手奮力劃著,向這邊駛來。瑪魯眼神好,驚呼:“他們的小船都是有撞角的!”
“想作自殺式的攻擊,或者是浪費我們的炮彈。”鐵木真冷笑道,“不會得逞的。床弩準備。”
后來,即便是復仇心切的瑪魯,也覺得那些倭寇死得太慘了。因為顯而易見,木頭和肉體對高速飛行的鋼鐵的抗擊能力是非常弱的。所以這些人和小船就在床弩的第一次齊射下瓦解成了碎片。斧刃一般的箭頭呼嘯著割裂了船板、木槳、人的骨肉,甚至于銅制的撞角。海水中一片狼籍。倭寇的小艇紛紛掉頭返航,但已經來不及了。第二波的箭頭輕易追上了他們。
怯綠連號繼續向倭寇的戰船逼近,邊行駛邊開炮。這時候,飄揚著日月旗的中國船也從另一邊攻擊倭船。鐵木真低聲說:“姓朱的皇帝,我可不是在幫你啊。這是給馬明看的”
他們一直把剩下那艘日本船擊沉。海面上都是抱著碎木頭漂浮的倭寇,瑪魯看他們可憐,就求鐵木真說:“救一救他們吧?”
鐵木真點了頭,怯綠連號緩緩開到倭船沉沒的海域,那些敵方水手拼命往船上爬。這時候,拔都也已經吃下瑪魯給的解藥,站到了船頭,他喊道:“爬上來的降人坐在甲板上!有異動者,格殺勿論!”
倭寇們使勁坐低在甲板上,鐵木真掃視了一眼,指著一個身穿魚皮甲、頭戴雙角,貌似首領的倭寇:“你過來。”瑪魯注意到,他說的是漢話。
那倭寇竟能聽懂。他膝行到船頭,對著敵人磕下頭去。鐵木真問了他幾句話,他答得很快。
二副過來說:“船長,那艘中國船正往我們這邊開,怎么辦?”
“用炮瞄準它。讓它開過來。”
“是!”
明朝的戰船形制與歐洲船不一樣,雖然也是三桅,但船體較為寬平,沒有撞角。鐵木真低聲命令:“炮彈上膛,箭上弦,瞄準中國船!”
對方船頭上站立一人,鎧甲佩劍,威風凜凜,高聲說道:“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悅乎?”
鐵木真哼了一聲,手按刀柄,也用漢話說:“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?”
對方抱拳行禮:“在下福建防倭城指揮使,劉錦。敢問閣下尊姓大名?”
“鐵木真。”
劉錦的手也按上了劍柄:“閣下是蒙古人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