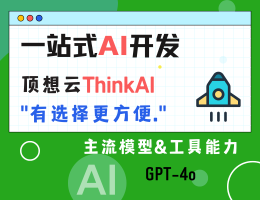碧姬笑對敏娜說:“多謝你幫我們過了一關。”
鐵木真問:“什么?敏娜怎么幫了我們?”
“傻子。”碧姬笑道,“你還沒看出來嗎?薩里木以外國人在南京買武器,引起官府的注意,本來是應該全船拘捕的。但敏娜直接帶我們見皇帝,雖然沒解說買武器的事,實際上就是求情。皇帝走時說‘今天就到這里’,意思很明顯,就是說此事不必繼續追究啦。”
鐵木真吁了口氣:“你真聰明,我就沒有看出來,敏娜,謝謝你啦。”他借兵未償所愿,本來極是失望,幸而他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,也就不再追悔了。
敏娜笑著說:“中國的事就是這樣,講人情。皇帝說句話比什么都管用。那天大小姐打我鞭子,少爺不是也替我講過人情嗎?”碧姬等人大笑。
鐵木真對碧姬和瑪魯說:“手傷已經養好,今天我就直接回怯綠連號上去了。”說完就請馬家的人搬梯子去拔房梁上的刀。那刀插得甚深,幾個家人撼動許久才拔下來。
碧姬略有黯然之色,瑪魯問:“姐姐,你舍不得他么?”
碧姬瞪了她一眼:“舍不得他的另有其人。我是還情已了,無事一身輕啦。明天我的柳葉刀號就離開南京,回葡萄牙去,我要查查當年亨利王子是否曾經讓人毒害鄭和。也算了卻一樁公案。有什么消息,我會飛鴿傳書告訴你們。”
瑪魯一怔,神色轉為凄然,對姐姐說:“剛剛度過劫難,咱們姐妹就要分開,也不知還能不能見面了”碧姬笑著說:“你講什么話啊!當然能見面。古怪的小丫頭”鐵木真說:“瑪魯莫說傻話,你知道現在是中國歷的幾月份了?”碧姬說:“這大概要問問馬老先生。”
馬老先生說:“今天是二月十七。你們幾位有什么急事么?”
鐵木真笑對瑪魯說:“你還記得我在船上訓練水手的那個陣法么?”瑪魯點頭:“記得啊,那是什么陣法?怪難看的,海上打仗不管用,耕地又種不出莊稼。”
鐵木真說:“有個日本人跟我約好,今年三月份在中國的登州做一次賭賽,他帶一百名日本武士,與我的一百個水手打一仗,只決勝負,不決生死。你也跟我去吧。”往常瑪魯定會雀躍同意,但這次她卻有點為難,說:“還是姐姐陪你去吧?我不喜歡看打仗。”
碧姬搖頭:“我要去葡萄牙的。鐵木真這件事跟我又沒有關系。”瑪魯還要推拒,鐵木真說:“這件事跟瑪魯可有關系,你教過我的水手打槍,到時候還得你指點呢。就這么說定了,明天就動身。”瑪魯這才不說話了。
坐轎子回到碼頭,薩里木苦著臉對鐵木真說:“船長,咱們的船被扣了,就因為在南京買了武器。”
碧姬驚道:“什么?我的柳葉刀號沒有被扣吧?”
“沒有,只扣了怯綠連號。”薩里木說,“可是,你的船上也有中國兵在檢查。”
鐵木真跟薩里木上了船,船上已有一小隊中國士兵,手持火把端立在甲板上。薩里木帶著鐵木真走到船的左舷,借著燈火之光,看見一排十朵巨大的鐵蓮花,用銅架固定在船舷上。薩里木說:“這叫碗口銃,炮膛內可填裝霰彈,碎鐵片小石子都可以,射程不遠,但是殺傷力很強,在接舷戰時用處最大。”
鐵木真指著一堆黑沉沉的圓筒:“那是什么?”
“那是剛剛買的洪武大鐵炮,每尊炮重兩千斤。”薩里木說,“能把三十斤重的開花彈射出三百步。小一些的船,挨上一兩發炮彈就會沉沒。”他低聲說,“從前打海盜時贏得的賞金被我花了一大筆。不過,咱們的戰斗力又升了一級。”
他說完又問:“我們的船雖然裝了這么多好武器,可是不能走,怎么辦呢?”
鐵木真說:“這件事已經由皇帝定下了,不會再追究。正好讓中國官府替我們守船,留二十名水手在這里,其余的我去登州游玩一場。玩了回來再開船走。”
薩里木嘆了口氣:“唉!水手要騎馬”
“不用騎馬,我們坐車去。”
雖然說是坐車,鐵木真自己卻買了一匹黑色駿馬,瑪魯、拔都和水手們雇了三十多輛大車乘坐。一路上熱熱鬧鬧,蒙古水手們久不上陸,看什么都很新鮮,追雞趕牛,如同一幫農村大小孩。瑪魯卻很沉默,偶爾鬧些小性子,都是立刻后悔,和好如初了。
看看剛入三月,這一日住店,店主說,已經靠近了登州地界。瑪魯接到了碧姬的飛鴿傳書,看完以后對鐵木真說:“姐姐不去葡萄牙了,她在南京認識的那個濮仲謙,答應替她的船裝上諸葛連弩,三天就能裝好。裝完以后,她就趕上來。”鐵木真笑道:“那時你們姐妹見面,可有一番熱鬧了。”
“船長!”薩里木過來悄悄對鐵木真說:“船長,我們沒有錢了!”
“什么?”鐵木真問道,“住店的錢都沒有了?”
薩里木為難地搓著手:“沒有了。我們船上的黃金都是從前打海盜所贏的賞格,在南京的時候買武器,就花了好大一筆錢。雇大車交定錢又用了很多。今天晚上,如果店主要我們付房錢,我們真的拿不出來了。你看怎么辦?”
瑪魯在旁邊聽見,說:“有什么了不起的!大家拿起兵器,跑到附近去搶一把就是了。”
鐵木真搖頭說:“瑪魯就是胡鬧。這里是中國,我們的船還在南京扣著呢,怎么能如此胡來?”
瑪魯說:“那么我們就耍賴。”
“怎么耍?”鐵木真說,“店老板總不會像我對你那么容讓吧,你就是哭鬧渾賴,他也不會買你的賬。”
瑪魯笑著靠近他的身子:“你聽我說呀,明天我們吃飯的時候,就要吃牛肉,店里一定沒有,我們就鬧起來,說要什么沒什么的店,沒有住頭,把碗筷丟到地上,起身就走,他肯定不好意思,再加上害怕惹事,就忘記收我們的店錢了。”
她說的確是實情,中國百姓不吃牛肉。這一路上,每當蒙古水手們向酒館客店要牛肉吃,店家就會說:“罪過呀!小店沒有牛肉,客官請向別家去買吧!”所以他們都只有吃豬羊之肉。
薩里木拍手說:“好主意!”鐵木真卻搖頭:“你們兩個算是蠻干到一起了!如此渾賴,于心何安?”
瑪魯不依:“那依你說該怎么辦?你能跪拜一下長生天,就從天上掉下一堆銀子來么?”
鐵木真微笑不語。瑪魯拉著薩里木到角落里去:“來!我們商量一下,拔都和鐵木真兩位老大爺都太古板,不能跟他們說。你晚上去跟大家說好,明天”
第二天一早,鐵木真等在東堂屋飯桌邊吃飯時,聽見店老板的聲音在隔壁西堂屋說:“大爺,小店確是沒有牛肉和生魚片,請你們到別家去買吧。”一個男人的聲音怒道:“什么都沒有,你還配開店么?飯房錢我們就不給了!”口音古怪,倒像是外國人。老板求告說:“小的老婆生了,連雞蛋小米都沒錢買呢,求大爺們松松手吧”
鐵木真瞧瞧瑪魯,低聲笑道:“看起來還有別人跟你想法一樣。”瑪魯翻了翻眼睛:“你以為誰都像你那么古板!”
卻聽那邊拍桌子摔板凳,吵鬧起來。鐵木真說:“過去看看,好像要打架。”薩里木和瑪魯都是惟恐天下不亂的角色,當下飛也似地跳起來跑過去了。
鐵木真也跟過去,卻看見隔壁坐著一大群黑衣人,服飾不似中土人物,發髻高起,各人佩有一長一短兩把劍,有的已經把劍拔了出來。為首一人,竟是魁夷。鐵木真叫道:“這不是魁夷嗎?怎么在這里吵起來了?”
魁夷扭頭見是鐵木真,尷尬地擺手制止了那些同伴,笑著說:“這些家伙沒到過中國,世面見得少了,免不得露出些鄉巴佬習氣,沒事了!大大哥。”他本想叫“大汗”,但怕驚動不相干的人,才改了稱呼。
鐵木真說:“想不到你們也在這里,是赴登州之約來的吧?”
魁夷稱是,還說要代鐵木真付了飯房錢。鐵木真想雙方即將比斗,算是一半敵人,就拒絕了。那些日本人中有幾個披蓑戴笠,很注意地看著鐵木真,目光陰沉。瑪魯悄悄一扯鐵木真的衣服,把他拉了出去。
“什么事啊?”鐵木真問。
瑪魯小聲說:“你一定要小心這些日本人,我發現他們都帶著兵器,而且有幾個人看你的眼光都狠巴巴的。這個魁夷恐怕對你不懷好意。”鐵木真一笑:“他們本來就是來跟我們比武的,又能有多少善心呢。”瑪魯急道:“你好傻!我不管你了。”說完搡了鐵木真一把,轉身就走。鐵木真倒高興她又恢復了原來的態度。
忽然,瑪魯又悄悄跑了進來,小聲對鐵木真說:“又來了一幫!你這個蠻子,到底約了多少日本人打架呀?”
鐵木真說:“只有一百個呀。哪里還有另外一幫?”瑪魯說:“你不信就瞧瞧隔壁。”鐵木真站到門口向西堂屋看去,見偌大的一間屋子里擠滿了人,都是同樣打扮,有一半的人大概是后來的,身上黑衣鑲有白邊,按劍站在堂屋的靠墻一圈,隱隱對魁夷等人形成包圍之勢。魁夷滿不在乎地坐著,傲不為禮。后來人眾中為首的一個抗聲說:“右京兆大夫入華貢使宗設在此,你是何方假使?”
魁夷說:“我是左京兆大夫大內氏所遣正使,你好大膽,竟敢與我爭貢。”其時日本正是所謂戰國時代,各地守護大名擁兵自重,中央無力約束。而向中國進貢好處甚多,所以每次入貢,諸侯都爭相前來占便宜,至有后來貢使爭風殺人之事,釀成倭寇之患。
那宗設冷笑一聲道:“你這區區百人隨員,攜帶著廢銅爛鐵,是來討飯、撿破爛的么?”一揮手,站立四周的右京兆貢使隨員都伸出雙手,手中握著點燃引線的粗大火銃,對準了屋內坐著的諸人。宗設說:“這是我國所制的武士裝備,名為侍筒。正使閣下有何見教?”
魁夷漫不經心地瞟了一眼,說:“道順,平八郎!”
他身旁兩個披蓑戴笠的隨從應聲而起,蓑草飛揚,颯然有聲,旁人還不及眨眼,這兩人已閃到了宗設身邊,一左一右挽住他的胳膊。
宗設被這閃電般的動作驚得呆了,汗都來不及出。而他左右的武士反應甚快,已經扣動了扳機。引線觸在點火口的藥粉上,燃燒進去。
說時遲、那時快,道順和平八郎一手抓著宗設,另一只手已拔出劍來,頭也不回地一揮,握銃的手已被砍落。反足一踢,手和鐵銃一起飛出了窗外。這一切都是在電光石火般的瞬間完成,手和銃飛出窗外之后,才聽到“砰”的一聲,鉛彈剛剛射出,嵌在木頭窗框里。
這雷霆電閃般的一串動作完成之后,屋內眾人才感覺到自己出了冷汗。
魁夷笑著說:“侍筒雖利,怎奈使用的武士不利。宗設大人看我手下的隨從如何?他們不是武士,只是從伊賀雇來的忍者而已。”
宗設臉色蒼白,胸膛起伏不定,叫道:“射擊!大家一起死了吧!”
但魁夷手下的隨從們不待主人的命令就擲出了短劍,屋內一片閃光,如下了一陣流星雨,耳中聽得嗤嗤、篤篤、啊啊、哦哦、買告德、八個壓路、呀咩爹之聲,短劍全都沒入敵人的要害部位,有的是胸,有的是眼,有的是下部。宗設所帶的武士們都來不及發射侍筒,已經捂胸、捂眼、捂下部地倒了下去。
魁夷命令:“把他們的貨都搜出來。”隨從們一哄而上,先拔出尸體上的短劍收好,然后搜出貢品——花木屐、鯉魚飄、小紙傘、芥末瓶之類,揣進自己的懷里。店老板早嚇得渾身大汗鉆進賬房桌下,魁夷傲然走出,他的隨從們也按劍隨行,宗設被兩個忍者挽住,不得不跟著走了。老板哪里敢說話。
瑪魯甚是擔憂,對鐵木真說:“我看他們的武藝很高強,能打得贏嗎?”
鐵木真一笑:“你別擔心,我看了他們的動作,以我們的陣法,足夠勝他。”
“那么快的動作,這些笨漢子怎么抵擋呢?”
鐵木真說:“自然抵擋不及,但是又何必抵擋呢?”
“何必抵擋是什么意思?”瑪魯低頭思索。
鐵木真摸摸她的頭:“小腦袋不是挺聰明的嗎?怎么想不明白了?”
“我咬死你!”瑪魯沖著他呲了呲牙。
薩里木瞪著牛眼走過來,低聲說:“錢還是不夠啊,我們到底用不用那一招兒?”
瑪魯說:“前面那些日本人已經用過,大概是不靈的了。鐵木真,你說怎么辦?”
鐵木真笑著說:“只有把你們倆押在這里當店錢了。薩里木給人家劈柴,瑪魯幫他們掃地,你在船上刷甲板不是很快的嗎?”瑪魯哼了一聲。鐵木真走到賬房桌邊,老板剛剛鉆出來,一見他,又鉆了回去。鐵木真說:“老板,你別怕,我們跟那些人不一樣,那些死人你別去動,要報官,告訴登州官府,就說是日本貢使互相爭風打斗,與你無關。”
老板趴在桌下說:“好好,真是好人大爺,你們的店錢我也不敢要了。你只管走吧。”
鐵木真一笑,帶水手們走到后邊去趕車,竟沒有付賬。瑪魯跟在他后面笑著說:“怎么樣?大好人,你也賴賬了吧?”鐵木真笑道:“不賴賬,就只有把你押在店里了,你說我怎么舍得?”
瑪魯說:“我呸!”她年紀幼小,心里本來有些憂愁之事,也藏不長久,這幾天畢竟忘了。
薩里木忽然大叫道:“咦?我們的馬呢?怎么只剩光車子了?”
果然,客店的車馬房里只剩了車廂,一匹馬也沒有了。連鐵木真的黑馬也不見蹤跡。趕車的把式哭喪著臉蹲在地上,說:“他們把馬都牽走了,那些黑衣服的狗日的先是偷,我們上來攔,他們就拔出刀子來搶。”
瑪魯說:“那些日本人偷走了我們的馬,真是可恨!我早就告訴過你,那個魁夷對你不懷好意。追上去,把他們的頭發都拔光!”鐵木真問:“怎么追?他們是騎馬走的,我們步行能趕上么?”
瑪魯轉轉眼珠:“咦,這兒有一頭驢,不知騎慣馬的英雄能不能騎”
“能騎也只有一頭啊,”鐵木真說,“看來只有我騎上它,往登州走一趟了。”
瑪魯笑著說:“我還沒見過蒙古人騎驢呢,你先在店里騎一圈,我拿鞭子趕趕,說不定很好看。”鐵木真一揚手,瑪魯大笑著跑開了。
鐵木真把驢從磨旁解下來,瑪魯已經會說幾句中國話,向店老板借了驢鞍和鞭子,拿到后邊來,摸著驢說:“驢啊驢,你去登州可要小心了,不要讓人抓走,也別讓那些日本人傷了”嘴里在跟驢說話,眼睛卻斜瞟著鐵木真。
鐵木真在她屁股上拍了一掌:“好啦,我要走了。”瑪魯退到一旁,鐵木真把鞍子綁好,跨上驢背,瑪魯大聲叫好:“人驢相配,好看死啦!”
鐵木真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瑪魯說:“驢跑得慢,這家伙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回來。”
過了一個多時辰,鐵木真就回來了,后面還跟著一幫挨揍土匪般的兵勇,歪戴帽、斜穿衣,頭流血、手骨折,牽了幾十匹馬,倒還是完整的。
瑪魯跳過去問:“你真有本事啊!這些東西都是從哪里偷來的?”鐵木真說:“這是從登州衛指揮僉事戚大人那里借的。他聽說日本貢使爭風殺人,又竄往登州,而咱們是要跟那些日本武士比武賭勝的,就把這些兵和馬借給了我。”
“這些是什么窩囊兵啊?怎么都頭破血流、四體不全的。”瑪魯小聲說。
鐵木真在她耳邊說:“他們也剛吃過那些日本人的虧!”
“哦。”瑪魯走過去,用漢話對著一個手用綁帶吊在脖子上的兵問,“老總,你們,日本人的虧,吃得大大的?”
那兵往地上啐了一口,罵道:“呸!日什么本人,我日他祖宗!他們說是來進貢,其實是想得咱們皇上的賞。他們帶些摳門小玩意兒到中國來倒賣,一小瓶辣芥末賣咱老百姓一兩銀子。不買就打人。遇到咱們官軍,官軍要多,他們就說是貢使蒙混過去,官軍少的時候他們就一哄而上,揍了就跑。我們就是今天晌午遇上了那群狗娘養的,我操他奶奶的熊”瑪魯笑道:“你們帶著馬跟過來,是想找那些日本人報仇吧?”那兵說:“報仇?我們是來看熱鬧的,你們不是要跟他們賭斗比武嗎?你們贏了,老子們也出口氣,穿上馬靴,踢他媽的屁股幾腳!”
拔都在旁邊聽著,搖了搖頭。其時明軍已不如洪武、永樂兩朝那樣精銳,各衛所的兵士都頑劣無比,懶于訓練,自然遇到精悍的倭寇武士就一觸而潰。
鐵木真說:“我們把馬套在車上,上路吧。”大家從客店柴房里把兵器搬上車廂,又套了馬,水手們一哄上車,車把式鞭子啪啪抽了幾聲,不敢傷動軍馬,只抽在空中。馬車魚貫出店。那些登州衛的兵士們騎著馬,晃晃地跟在后面。
瑪魯從車廂里伸出頭來:“鐵木真!鐵木真!你來一下。”
鐵木真撥轉馬頭過去,瑪魯說:“你們約好在哪里比武沒有?”
鐵木真說:“只說了登州,什么地方就記不得了。好像是太平樓。”
“太平樓?打起來可就不太平了。”
走出數里,鐵木真看見路邊有幾個鄉民裹頭吊手、一瘸一拐地走,就問:“老鄉,你們看見過一群穿黑衣服、帶刀的人嗎?”
“我呸!”一個花白胡子老農說,“看見了,他們還賣辣芥末給我們呢!我說咱們山東人不吃辣,大蔥還對付著可以,那個破玩意兒一聞就流眼淚,還賣那么貴,誰要啊?一個叫木村什么之乎者也的就掄拳頭給了我老漢一下子,那是些什么蛋人哪?”
“他們往哪里走了?”
“往東,伙計。”
鐵木真心想:“魁夷這伙人真是太囂張了,做生意也沒有這么做的呀。”
有一個瘦如竹竿的鄉民追過來說:“大爺,大爺,那些人還問了我們登州衛在哪里駐兵、皇莊里有多少佃農、城外有多少小道呢。”他眼睛一眨一眨,賣乖地笑著。
“是嗎?”鐵木真說,“是不是一個眉清目秀、眼光兇狠的高個子問的?”
“是呀。”那瘦鄉民見鐵木真撥馬要走,又追過來,“大爺,大爺,他還問了我們登州城里最大的窯子在哪兒呢,我說我們老實農民,讓莊頭壓得連飯都吃不飽,誰知道那個?”他翻起眼睛來一眨一眨地。
鐵木真想:“這是想要賞錢呢,怎奈我沒有。”他向瑪魯的車子大聲說:“瑪魯啊,咱們去年的銅錢還有沒有?拿來給了這幾位老鄉吧?”
“哪兒還有啊?”瑪魯在車里說,“田小二他老婆生的時候,不是都拿去買雞蛋小米了嗎?”
那幾個農民這才走了。鐵木真等人又催馬趕車向東追去。
追了一會兒,又見幾個鄉農挑著花擔子往城里趕,擔子上都是牡丹花,花根用泥裹住,外包麻袋片。瑪魯從車廂里探出頭來看稀奇:“這是干什么的?”
“賣花的花農。”鐵木真說,“你沒聽白居易說:‘一叢深色花,十戶中人賦’嗎?”瑪魯翻了翻白眼:“白居易是誰呀?你表哥?”
鐵木真向一個花農問道:“老鄉,你們見過一群穿黑衣服、帶刀子的人嗎?”
那花農哼了一聲說:“我日他親姑搶了我八棵黃牡丹花!說是要回去送給他媽媽,讓我也拿出點孝心。我日”
“他們往哪里走了?”
“進城了。”
正是暮春時節,下起小雨來。瑪魯探頭出來說:“鐵木真,你冷不冷?上車來吧。”鐵木真從馬上直接邁上了車,鉆進車廂里。
車廂內果然比外面暖一點,而且觸鼻盡是瑪魯身上的花粉氣息。瑪魯單獨與鐵木真坐在一起,又沉默了。
鐵木真不知怎的,也略覺尷尬。坐了一會兒,瑪魯輕輕靠在他身上。他摟住瑪魯的腰,問:“冷不冷?”
“冷。”瑪魯小聲說,“摟緊一點,哥哥。”
鐵木真雙手把她抱住。瑪魯說:“還要再緊一點。”鐵木真把她抱進懷里。瑪魯柔軟的身軀忽然變熱起來,展臂抱住鐵木真,嘴唇吻在了他的嘴上。鐵木真頭腦中一陣混亂,心里覺得仿佛飄在云端,過了好一陣,才嘗到瑪魯的眼淚那海水般的味道。他驚問:“瑪魯,你哭了?”
瑪魯把臉藏在鐵木真懷里,無聲地抽泣,小小的肩膀哭得顫抖不已。鐵木真心亂如麻,摟著她問:“你為什么哭?有心事嗎?告訴我!”
瑪魯在他衣襟上擦干了臉上的淚水,抬頭強笑道:“沒有啊,我沒哭。”“你剛才明明哭了的。”
瑪魯用衣袖在鐵木真臉上輕輕抹了抹,把沾上去的淚水擦干,低聲說:“我發瘋。”
鐵木真看她玉頰上微泛紅暈,還殘留著幾道淚痕,想起她從前的種種爛漫可愛之處,對比現在她的心事重重,不由得心如刀絞,摟緊了她說:“瑪魯,我們兩個現在還有話不能說嗎?你這樣一會兒哭一會兒笑,我又不知道是為什么,心疼死了。如果是別人就會亂想的。”
瑪魯在他懷里仰臉望著他,望了一會兒,小聲說:“你心疼我,我好高興。你是個大丈夫,不會亂想。你的心不要疼,你忘了我吧。”
鐵木真急道:“胡說八道!怎么能忘了你?沒有你,我活著又有什么意思?”
瑪魯伏在他懷里,自豪地低聲說:“鐵木真,你不一定要有我才能活下去,你永遠是活在太陽下面的英雄。不管什么樣的敵人,如何陰謀算計你,你總是坦蕩蕩地在陽光下面大步行走,而且總是比他們活得快樂。”
鐵木真見她如此,知道她不會說出實情,長嘆了一聲,把她摟緊,瑪魯把鐵木真衣內的銀鏈扯出來,用手輕輕撥弄著說:“如果你不是鐵木真,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孫,只是個普通的蒙古牧民;我也不是瑪魯,不是黃金同盟的刺客,就好了。我們在草原上無憂無慮地生活,你在外面放羊、牧馬,我就在家里替你煮飯、補衣服。對了,你喜歡吃什么東西?”鐵木真說:“我自己都不太清楚。”他性子粗疏,說這些話并不起勁。
瑪魯嘆息了一聲:“唉,可惜我從來沒有給你煮過吃的。不作牧民也好啊,我們就在這里當農民。你在外面耕地,我就在家里給你煮飯、洗衣服。你這么大力氣,耕地是不用牛的,自己拖著犁就行啦。不過那樣你肯定會吃很多東西,要把家里吃窮。還是用牛吧”
鐵木真抱著她說:“你在給自己講故事嗎?”
瑪魯又長長地嘆了口氣說:“要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多好啊。或者,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過我,你一個人活著豈不是好?”鐵木真揉了揉她的頭發:“凈說傻話一個人活著,孤孤單單的,有什么好?”
“你認識碧姬呀。”瑪魯說,“她也是一樣的漂亮,而且,雖然脾氣怪了點,她可還比我懂事呢。我又饞又懶,貪吃貪玩,你總有一天要討厭我的。”
鐵木真覺得她這些話越聽越有不祥之感,問道:“你這小腦袋里究竟在想什么?你后悔認識我了嗎?”
“我從來也不后悔。”瑪魯說,“我只是有點預感,覺得自己會早死。那時候你一個人,能不能不想我?碧姬會照顧你的。”
鐵木真握緊瑪魯的手:“你別說了。我不相信你的預感。萬一你比我先死,我會孤身一人遠走天涯。碧姬雖然美,可是瑪魯,這個世界上沒有能代替你的女孩子。”
瑪魯趴在鐵木真身上,迷迷糊糊地半閉著眼,一會兒嘆氣,一會兒唱歌,不知不覺就睡著了。鐵木真脫下外袍裹在她身上,聽著車廂外的潺潺雨聲,心底萬事沓來,一會兒是借兵不成,將來何去何從;一會兒是與魁夷的比武;一會兒是瑪魯古怪的表現,諸事走馬燈一般旋轉,簡直使心亂如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