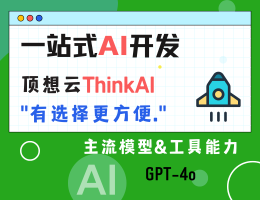## **海媽媽**
在這島周圍的海面上,有十幾個衛星島,都是些荒無人煙的孤島。唯有相距不過半里的馬島,緊偎在這主島的身邊,每當退大潮的時候,兩島之間便出現一條淤沙沖擊起來的壩埂,那水柔如羽,長堤臥波的景色,實在是太美了。
在這主島上,住著不過二百戶人家,也盡是漁民。在從前灘到村里的唯一的那條路邊,有一塊傍海守路的礁石,海媽媽每天總是坐在上面的。她看看那油盆兒似的海;看著道口上人來人往,也算個營生和樂趣。有時她動一動眉尖,卻顯露出在古銅色的臉龐上的眼角、前額一些地方,有那么幾道白色的皺紋,海媽媽確實老了。
現在正是夕陽與大海互為輝映的時分。偌大的一輪血紅色的太陽,輕輕地親吻著西邊海上的海水,大潮早已退過,微波暗涌,該是要漲潮了吧!海媽媽用她生滿老繭的手,撩起早被海風吹退了色的藍布褂襟兒,擦了擦眼,向海里還沒有被潮水淹沒的壩埂上眺望。
海是金色的,馬島是金色的,而那條連接兩島的壩埂竟成了一條黑線,能看到靜靜綽綽的幾個人影,正匆忙忙地向村里趕來。
“唉,還不快走幾步,大潮就要淹壩埂了,看你還不得泅水過來呀!”海媽媽這般焦急地想。
沒過一會兒,從前灘通往村里的大道上,走過來第一個到馬島去“趕海”的人。
“誰家的孩子呀?”
“是我,海媽媽。”一個銀鈴般的聲音。
“噢,是二嫚子呀,我看看你這一潮趕了些啥玩藝?”海媽媽一邊說,一邊不由分說地拉過二嫚肘里挎的簍子。
“我不信連馬島上都沒有大蛤,你怎么凈趕了些小蛤皮回來呢?”顯然是埋怨的口氣。
二嫚的臉腮上,頓時飛起兩朵紅云。她靦腆地笑了笑,挎著簍子走了。
小愣子也過來了,當然他脫不了海媽媽的檢查。
“呦,就這么幾個小蟹子呀?難道就沒有‘齊甲紅’?”
小愣子的脖子繞了繞說:“今天潮水不好,東北風十個簍子九個空嘛!不信,你老太去抓個‘齊甲紅’俺看看!”說著,他一撅一撅地跑了。
“嘖嘖!這些毛孩子,生在漁家不懂水性,老輩人說,春風頭秋風尾,像這秋半天,剛刮過大風,海貨還不往攤上竄?”她這般自語著,心底不禁又涌起自己年輕時代在海上的諸多往事——
神秘莫測的大海是迷人的。在這青翠的小島上,漁家人流傳者許多關于海上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,這里面就有海媽媽。打魚的人說,海上是有夜叉的——一種類似人性,卻十分兇猛可怕的動物。可誰也沒見過。那一年,一個濃霧的夜晚,島上的一只漁船返棹登岸,船老大驚恐地告訴大伙說,他的船行經頭孤島時,看到一個大夜叉,坐在孤島上,兩腳拉叉著吃活魚哩!當年還不滿三十歲的海媽媽--當然,那時她也不被人稱著海媽媽的,只是個野小子式的漁家姐吧--偷偷地獨自跳上舢板,操起大櫓,吱吱呀呀地向頭孤島搖去,她要去會一會海夜叉,要把那東西捉回來,煮肉給漁家姐妹嘗嘗鮮。不過,頭孤島仍是頭孤島,它兀立在夜霧之中,偏添了幾分神秘的色彩。她搖著船,沿著那塊孤礁轉游了幾圈,哪有什么夜叉?夜那般靜,海那般靜,一塊死礁聳立在夜海濃霧之中。她失望了。她本想用手中的大櫓那夜叉打死的,可到哪里去尋它呢?當她不甘心地駛離這孤島的時候,回首再仔細端詳,那島上的礁石,確也真像個什么巨大的怪獸。怕是船老大在夜霧里看花了眼吧,她這樣捉摸著。
如果說這是闖海歷險的一次失敗,那么她在豹子江上打海豹的膽識,島上人直到現在還夸著呢!
豹子江,明確點說應該叫豹子崗。那地方是片暗礁,崗子是暗礁與淤泥集成的。遇到風浪天,就是有經驗的船老大,船過這帶水域,也得小心翼翼;春節里,南海里的海豹游來,退了潮,它們都躺在崗子上。這島上人誰不知豹子兇,輕易不敢去斗弄它的。一個有月色的夜晚,海媽媽約好一個有虎性的棒小伙子,帶上鋒利的長把鋼勾,倆人悄悄地劃著一只舢板,拖著海媽媽往海里扎。小伙子這時舉起木棒,朝那家伙的頭上亂打一陣……這就樣,島上人第一次吃上海豹肉。據說并不反腥,還真有些特殊的鮮味哩!
“海媽媽,回家來吧!”她那些像海一般深沉的回憶,被村子里孩子們的呼喚聲打斷,如同這強勁的晚潮,沖擊在腳下的巖石上,開了朵朵的白浪花,復又撒落進了大海。她坐著褐紅色的礁石上,看著那瘦瘦的壩埂上人影走絕,看著那紅燈籠般的夕陽沉入了海底,也看著那細線似的壩埂被潮水完全淹沒,整個大海復又成為一片汪洋。
“海媽媽,快回家吧!”她耳邊又聽到遠處村口漁童的稚喚叫。她轉過臉,只見村里飄起了炊煙,暮靄多像一幔輕紗,除了主峰上白色燈塔忽閃起明亮的眼睛,這輕紗把全島打扮成一幅淡墨畫。
該是吃晚飯時分了。海媽媽這般自語著,剛想欠身,卻又望見大道上急忙忙地走來一個人,是誰呀?天到這般光景還不在熱炕頭上歇著?走近些,她才認出來,原來是小愣子。
小愣子站在海媽媽的身旁,有些拘謹,也像似不太容易張口等半天只稱了一聲:“海媽媽!”
“怎么,叫我去吃你煮熟了的蟹子啊?”
小愣子憨笑著,撓撓頭說:“不,大伙兒想請您老幫個忙。”
“呦,人老珠黃的,我老婆子能幫你們點什么忙呀?”
“海媽媽,你沒看到山后海面上都發了紅,‘小大眼’起群了。”
“‘小大眼’起了群,你們就下海撈嘛,找我干哈?”
“用網打這種魚,船上的人看不準魚群,海水反光呀,請您老明早山頭一站,指揮指揮,俺就有主心骨啦。”小愣子似乎在懇求。
海媽媽搖搖頭說:“老啦,不比當年那陣子啦。你沒看我的眼皮子都耷拉啦?”
小愣子撓了撓頭說:“別看眼皮子,您看您的眼珠子晶亮晶亮,您的眼煞底,兩托水以下的魚,您準能分公母!”
“我揍你!”海媽媽口氣一轉:“人、船、灘頭上該準備的都齊刷啦?”
小愣子憨笑了:“現在船隊的隊長就站在您面前啊!”
海媽媽一拍大腿:“好小子,當隊長啦?那好,咱們明天一早后山頂上見!”
海島是寂靜的,海島的清晨卻被秋汛喚醒。在這島的后山,那千仞削壁下的沙灘上,近海的海面上,歡聲笑語早驅走了往日的寂靜。灘頭上臨時支起的大鍋里,熱水沸騰了;燒水的柴禾正冒著火苗,青煙徐徐地升上海空,與那晨霧繞在一起,飄飄渺渺,煞是好看。人們忙活著,吆喝著,這里突然這股熱火了,幾只白白的海鷗向遠海飛走了。
海媽媽今天起了個大早,打扮得又像當年出海打魚的漁家姐,頭上蒙條白頭巾,前額拉出個大沿兒;腳蹬一雙解放式的膠底鞋,扎著褲腿,偏顯得利落帶勁。在小愣子陪伴下,她徑自奔向后山最高的青石崖頭。當走到險要的地方,小愣子急忙扶她一下,她卻一手甩開,心里想,我年輕時候,爬這青石崖,不是走平道嗎?!
果然,憑著這股老勁,她三步并兩步地居然很快登上了岸頂。她先看灘上,只見大鍋里冒著熱氣,沙灘上鋪好葦席,她心里覺得順勁,點了點頭。漁家每年一茬,捕這種不足一寸長的小銀魚,怕臭灘,得捕上岸便用開水潦熟,再均勻地撒到葦席上。曬不上一個日頭的時間,就成了味美鮮口的“海蜓”了。
海媽媽心里服小愣子他們這伙娃娃們,沒丟漁家這老規矩,也沒點劃她,灘上確實準備得研磁合縫。
海是平靜的。漁家人叫這種風平浪靜的海是鏡兒、油盆;不過今天人不平靜,不遠的海面上,一排五條機動大舢板,正咕嘟咕嘟的響著,好像等著海媽媽的一聲令下,船兒就會大顯神通,來個大鬧龍宮。
且不去管小愣子的急性催促,海媽媽得先看著海、看著流、看著魚厚實不厚實。可不,半個海紅了,“小大眼”湊群成團地在海里翻騰。
“怎么樣?”小愣子問
“行,是火候了。”海媽媽答:“不過,別焦急,我得先看準流,哪里魚密咱向哪里下網,不能把魚群給嚇跑了。”
于是,小愣子憋住氣,只等海媽媽那雙搜尋的目光。可她,眼前這片海,哪里是流,哪里魚苗兒厚,卻是有些模糊。她撩起襖襟,再擦了擦眼,卻還是不靈。分不清魚群怎能下網?她的額角上偷偷地滲出汗珠。當然,既然是青年人瞧得起自己,總不能臨陣逃脫說熊話吧?單憑自己十年的老經驗,也總得應付一陣子的。
她猛地扒下身上穿的那件褪了色的藍襖,抓在手中,向空中揚了一揚,早晨的海風吹得那襖獵獵作響,這是一面指揮旗。
船隊散開了,按照海媽媽的指揮,直奔西北下網,岸上崖頂的人,心兒都系在那網頭上,三網過后,海媽媽覺得不對勁,小愣子也有點抓手擦掌,只是為了海媽媽那咬鋼嚼鐵的性子,才忍住聲兒。他們遠遠望去,那網頭都是輕飄飄的,海上一片寂靜。
海媽媽的額頭上又出汗了。
小愣子不敢直說,又不得不說:“老太,您看今天的風向?”
海媽媽瞅了他一眼:“看把你急成愣頭青了,好吧,你來指揮指揮,五尺高的漢子了,也該練著干點漁家行的看家活啦。”
小愣子這才接過她手中那件褪了色的藍襖,揮臂一轉,船兒紛紛掉頭向東南方開去。沒過一會兒,海上傳來笑聲,號子聲,那沉沉的網,那歡樂的歌,把整個大海鬧騰起來了……
“停!”海媽媽斬釘般地下了個死命令,把小愣子弄懵了,不知道自己指揮中哪里有失,便用兩只大眼睛問那海媽媽。
“讓所有的船都往上開,再轉回來圍捕,魚兒打到這分寸,就得用這法兒。”海媽媽拍了拍小愣子的肩頭,補充一句說:“老娘擺的是一個龍門大陣。”
太陽升起來了,海上流金涌碧一片光耀,晨光里,五條舢板向灘頭駛來,船幫緊壓著水面,滿艙里的“小大眼”,活蹦亂跳,在陽光下閃爍著柔和的光。
漁歌更響了,一曲快節奏的調門兒在這綠海藍天之間游泳,海媽媽站在青石崖頭,笑得露出了眼角旁那幾道白色的皺紋,她又拍了小愣子一巴掌,喜得不知該說啥。半天,她才喃喃地說:“這一潮……”
當天晚上,是個沒有月亮、也沒有星星的晚上,海是漆黑的,島也是漆黑的,可主峰上的燈塔沒有睡,仍然一個勁兒忽閃著明亮的眼睛;臨海一幢小屋的窗口,也透出燈光,把那橙黃色的希翼投入海上,隨著緩緩夜潮的移動,像是一疋彎彎曲曲的錦緞。
窗口外面,小愣子輕輕地拍著窗楞叫著:“海媽媽,開門吧!”
他手里提著一條魚,還在懷里揣著一瓶酒,心里揩海媽媽的油,用她的鍋、她的灶、她的油和醬,把魚燜熟下酒吃。
吱嘎一聲,海媽媽開了門,連看也沒看小愣子,嘴里就嘮叨:“媳婦又不準你喝酒是吧?‘氣管炎!’來吧,灶間的火還沒滅哩!”于是,在這間小屋里飄起了魚香、酒香,還有蔥花兒的辛辣香味兒。這一老一少就在灶旁扯起白天打“小大眼”的事。
海媽媽說,他來得正是時候,想求他幫幫忙。事辦成了,明天晚上他再來借鍋灶,就不必帶酒,她送他一瓶老白干。
“什么事?海里的還是灘上的?”
“嗨!我今天想了半日,老伴在的時候,每逢他出海打魚,總帶上他那副‘千里眼’,后來他過世了,那東西便被我忘記塞在什么地方啦,這屋里炕邊桌下我今天全翻遍了,也不見影兒。我想,怕是放在大柜頂上這口老箱子里吧。小愣子,你喝上酒幫我抬抬箱子,只要找出那‘千里眼’來,明早咱們后山崖頭見,我用那東西幫你指揮指揮,準保這兩潮管叫‘小大眼’來個掃地--窮!”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小愣子紅潤的臉,憨厚的笑,怕是真有點醉了。
夜,該是很深了,島上的人都在枕頭邊做著海潮的夢。只有這橙黃色的小窗口里,透出那么甜甜的、爽心的笑聲,和窗外的夜潮聲合上了節拍……
--: 發表于1986年第15期《文藝時報》
- 封面
- 大海的懷念
- 海媽媽
- 芝罘情思——海濱拾零之二
- 海岸路抒懷——海濱拾零之四
- 老街老巷
- 權威從哪里來
- 教誨
- 醉春風
- 宋磊學畫記之一
- 宋磊學畫記之二
- 只因他是主人翁
- 氣磅礴 色斑爛
- 寄情“老解放”
- 他們日夜在戰斗
- 華發添 志彌堅
- 漁歌灣
- 質樸的追求
- 不善巧思 必落俗套
- 乘長風起舞
- 智慧與理想的騰飛
- 哀歌
- 愛國主義的凱歌
- 鋼鐵二題
- 夜航明燈
- 在光榮的崗位上
- 載譽歸來訪韓濤
- 許身藝海勤探求
- 觀眾需要真善美的藝術
- 盔甲山抒懷
- 珍珠的光采
- 老帆桿
- 贊美你豐美的大地
- 一封無法寄發的信
- 光與火的凝聚
- 要演出人物性格來——戲曲瑣談
- 迷人的柜臺
- 銀色的鷗翅
- 風雨夜話人
- 新姿新色放新花
- 陳酒新酒總關情
- 玉環醉舞全憑酒
- 鼓舞的瓊漿
- 葡萄酒城漫步
- 下筆有心聲
- 迷人的《每周一曲》
- 沂水蒙山 巍巍雄風
- 結婚萬花筒
- 歲月長鮮歌不謝
- “梨園芬芳”芬芳了梨園
- 海事
- 為王煥理《拙齋小草》序
- 煙臺,我心中的城徽
- 一曲秉公執法的贊歌
- 父親的懷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