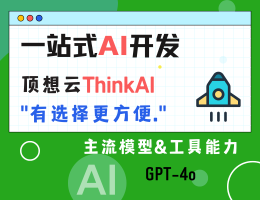作者:瑪妮
鄧:現在是1972年10月,在美拉扎德。瑪妮將繼續講述跟隨巴巴的新生活的各種事件。
瑪妮:嗯,鄧,我認為關于新生活,沒有很多要說的……
鄧:沒很多!到目前為止我們才談論了十四個小時!
瑪妮:事實上我認為關于新生活一個人沒有什么可說的。你知道,新生活不可談論——必須實踐它。我們只能談論外在的東西——所進行的活動——你可以在日記中或筆記本里記錄的東西。但是新生活是個不受時間限制的東西。巴巴說:‘新生活自身將繼續過下去,即使沒有人過著它。’因此新生活永遠繼續下去。那是因為巴巴給它賦予了生命,由于神人親自行走它,這給未來的所有人踏出了一條道路。
鄧:繪出活的藍圖。那就是你對巴巴在新生活中所做一切的詮釋嗎?
瑪妮:也許用‘腳印’這個詞最適合。你看,神親自行走了新生活,**這**把生命賦予新生活。新生活已被實踐了,因為巴巴已經代表所有將要遵循新生活的人過了它。當完美的化身在幻相中行動時,該行動是完美的。**他**所做的哪怕一小點都是我們難以企及的。就像巴巴曾說的:‘就算你們所有的人終生保持沉默,也比不上我的一小時沉默。就算你們所有人終生禁食,也比不上我的一天禁食。’
鄧:謝天謝地,我不喜歡禁食。
瑪妮:我也不喜歡!巴巴是宇宙性的,他做一件事時,是為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。他參與朗誦《懺悔禱文》時,雙手合十站在我們中間,我們中的一個人按他的指示朗讀禱文,他代表我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懺悔。我們即使懺悔終生,也無法彌補自己的過錯。但是他,通過在《懺悔禱文》中參與我們的懺悔,而為我們做了我們永遠不能為自己做的事情。神代表他的造物念懺悔禱文。完美者代表不完美者進行懺悔,通過其實在(Reality)的保證,使每個行動有成效、有生命、真實。
鄧:瑪妮,我想問一下,你通過跟巴巴交談,對新生活的印象、或許認識是什么?新生活是一種感受方式嗎?是一種流浪方式嗎?是一種行動與感受的結合嗎?新生活的特征是什么?
瑪妮:嗯,我所表達的只能來自我個人的觀點,這當然僅限于外部。正如鄧肯醫生在《行道者》中所說,對于巴巴所做的一切,我們只能看到冰山的頂端。其余的不為我們所見,沉浸在海洋里。巴巴說‘我同時在所有的層面上工作’,我們只能看見他在物質層面的工作。盡管如此,我們能感覺到那不可見的,如同你站在岸邊能感覺到海洋的深度,雖然沒有投身海中。我們知道無論巴巴做什么,即使是他的最隨意的動作,都服務于多種目的并產生多種成果。
新生活的目的之一是給予我們,個別的與集體的,訓練和紀律;反過來他還把我們用于他的工作,我們所能服務他的任何方面。但那不是全部。在各種各樣的程度上,新生活是為了你們,為了他所有的親近者,他所有的愛者和整個宇宙。
好比你在湖中投下一顆石子——水花飛濺過后是環形的漣漪。一圈接著一圈,形狀越大強度越小,直至最后覆滿湖面。巴巴所做的一切也是這樣。這一點我們是從經歷中得知的,有時我們曾認為某個計劃或行動是針對某個特別情況或個人的,但后來巴巴的一個隨意評論會讓我們明白,那不只是為了這個人或那件事,而是為了他的工作,他的工作是宇宙性的。
這就是為什么我說,我們談起新生活時,只能給出一個我們所觀察到的有限畫面,并且用‘我們從這里走到那里’和‘我們做了這個,他說了那個’等文字來描述。如我所言,由于神人走過了新生活,我感到它已經被生活過了。
鄧:我們其余的人類,將逐漸而必然地經歷他所設定的模式。
瑪妮:自動地!我們已經看到它的一些跡象,我們曾認為一成不變的舊模式和價值也發生了很多變化。我們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努力掙脫物質主義的舊束縛,開始感到對神的渴望,并尋找肉眼所見之外的東西!年輕人覺醒的這個浪潮我們若干年前從未想像過。
鄧:即使是十年前?
瑪妮:即使是十年前。因此,鄧,現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新生活的講述中增添些許而已。當然埃瑞奇已經給了你一個很全面的畫面,美婼也敘述了能記得的從女子的角度所觀察到的。我只能從我的日記里摘取一些有趣的記錄,也許她沒有涉及到。
但是在繼續之前,應該說我感到當我們被問起和談論新生活時,它的一個本應提及的方面沒有被提出來。這涉及到那些沒在新生活中伴隨巴巴的人:那些曾像我們一樣跟巴巴一起生活,但卻被留下在孟買、普納、美拉巴德或被派到西方的人;那些不跟他一起生活,但始終在他的指導下,并在被召或準許時來看他的人。所有那些人,那些熱烈地愛他的心,他們經受著最大的挑戰,因為他們不得不面對他們所確信的永別。巴巴曾說:‘你們必須相信我的話,當我說我和我的伴侶們走進新生活時,你們將不再與我們有進一步的聯系或交流。你們甚至不可企圖這樣做。我將不再回來,你們再也見不到我。’
鄧:怎樣的分離呀!埃瑞奇說你們都完全相信再也不會見到這些人,這些人也再不會見到巴巴了。
瑪妮:那是徹底的連根拔起。我們以為再也看不到美拉扎德了。我們的大多數家?用物品——家具等等,還有我們的私人物品——都被送人或賣掉。后來,我們最終回來時,忍不住想:‘噢,如果我們保留了伊麗莎白19xx年帶來的水壺該多好!是那么漂亮的搪瓷壺,現在再也得不到像那樣的了。還有那把面包刀,’等等。女人就是這樣!
鄧:伊麗莎白一定像一匹馱馬。每個人都談到:‘伊麗莎白帶來這個,伊麗莎白給了那個,’等等。
瑪妮:是的,確實是!但是阿娜瓦絲和納瑞曼,他們肩負著照管美拉扎德的責任,他們保留了接收的任何東西,以便巴巴萬一產生神圣沖動又回來時使用。他們不加思索地這樣做了。即使已送人或賣掉的東西,他們也盡可能去買回來。
對于那些讓巴巴離去,并相信再也見不到他的人來說,是非常困難的。而對我們跟巴巴一起旅行的人來說,不管在新生活中經歷什么,都有巴巴和我們在一起。回頭看看,我們可以經受百萬次所有那些困難,卻仍然會再次選擇在新生活中陪伴巴巴。但是對于那些耐心地留在后面的人,他們在新生活中的角色并不容易。
我知道對很多親近者,那是怎樣深的震驚。一些人的健康因而嚴重受損。就拿韋希奴的母親卡庫(Kaku)來說。她和我們很親近,特別跟美婼和我。她看到巴巴離開——她生命中最美好的、最重要的,全部的一切——加上她的兒子韋希奴,加上美婼,加上瑪妮。她的心碎了。她在我們回來前就去世了。對其他人震驚也是巨大的。他們感到一切都完了。但是他們繼續下去,巴巴會讓一切擺正,正如他一直做的那樣。
在實際進入新生活之前,就已經談了這么多。我重申對于新生活我沒有很多要講的,因為你已經聽到了一切。不過,我日記中有一些筆記,我想也許埃瑞奇、美婼和美茹沒有提及。我們踏上新生活時,1969年10月16日……
鄧:這天快到了,不是嗎?
瑪妮:絕對是,今天是14日。我的日記這樣寫著:1969年10月16日。我們踏上新生活時,天下著暴雨,電閃雷鳴。
鄧:典型的巴巴天氣。
瑪妮:是的。
另一個聲音:1969年?我一直聽到69年。
瑪妮:是的,我的確這么說的,對不起。
鄧:噢,你也是那樣寫的?
瑪妮:是的,我將更正它。1949年10月16日。我們踏上新生活時——就在我們出門時——天在下雨,電閃雷鳴。
鄧:你感到難過嗎?
瑪妮:不,一點都不。你知道,像平時跟巴巴在一起那樣,我們在出發前一直非常忙碌。
鄧:沒時間思考。
瑪妮:沒有,跟巴巴在一起,沒有閑逛和思慮的時間。你只是做你的部分,因為巴巴像交響樂指揮那樣指導著整個局面,每個人都忙于自己的樂器。我們看不到整體,但是每個人都忙著組成那個整體。
我們的第一次真正停留是在貝爾高姆,并在那兒駐扎了一段時間。那對我們是一種訓?練時期,巴巴稱之為真正新生活的前奏。我的日記寫到我們在10月20日到達那里。天氣非常寒冷潮濕,我們對此配備十分不足。實際上我后來聽說,阿迪冷得凌晨兩點左右起床,出去繞著住處一圈圈跑步取暖。
就在那里巴巴給了我們每人一條毯子,它叫做卡木里(Kamli)。是鄉下的一種手工編織的粗糙毯子,由羊羔毛制成。附帶說一下,很久以前巴巴的上衣也是用這種毯子做的——他穿了多年的‘卡木里上衣’。
鄧:就是你們放在美拉巴德博物館里的那件舊補丁衣服?
瑪妮:是的,它原本由卡木里毛毯制成。是由烏帕斯尼.馬哈拉吉的一位老弟子、亞斯萬特奧(Yaswantrao)做的。巴巴離開烏帕斯尼.馬哈拉吉時,亞斯萬特奧把它送給巴巴。
再回到新生活——在貝爾高姆巴巴給我們每人一條卡木里毛毯,平常我們會覺得它太粗糙,但是天氣如此冷,毛毯非常受歡迎,我們再也想不到比這個更好更可愛的了!
鄧:瑪妮,巴巴在新生活中怎樣睡覺?他有睡袋、被筒或毛毯嗎?他如何睡?
瑪妮:嗯,你知道,有篷車(只是為我們四個女子夜間睡覺用),靠近篷車為巴巴搭起個雨篷,有點類似帳篷,埃瑞奇每晚把它釘在地上。有一次我們在北方旅行期間,夜里雨下得很大,雨水直接穿透小帳篷。
埃瑞奇在外面守夜,坐在雨傘下。睡在露天的男子們當然被淋透了。男子們一直睡在露天,在樹下,而巴巴只有那個半防護的帳篷。
在貝爾高姆時,我們意識到巴巴確實如他所言是我們的伴侶,從巴巴跟其他男伴侶們一起勞動這個意義上。我的日記寫到:‘他們搭起帳篷,巴巴幫忙從井里打水,把蔬菜運到男子那邊。’別忘了,不管發生什么,不管我們在哪兒停留,在哪兒居住,在新生活之前和之后,女子們都單獨住宿,離男子們有一段距離,巴巴會從一邊走到另一邊。由卡卡在男子那邊做飯時,巴巴會把蔬菜從女子這邊送過去,有時放在籃子里,頂在頭上。巴巴不僅運送蔬菜,幫男子們從井中打水,也參加其它所有工作。
從11月1日開始我們女子接管做飯,巴巴在廚房幫助我們。我記得有一天我們燉菜,把所有的蔬菜放進去,然后某個地方出錯了!它一團糟,我們不知道該怎么辦,男子們的那份必須得送過去!我在日記中寫到:‘巴巴指導著放入各種東西,從而挽救了局面。結果它很是美味可口,受到所有人的喜歡贊賞,包括男子們。’
鄧:很好的廚師!
瑪妮:噢,是的!他只是稍微撥弄一下,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。
鄧:我停下想想,他一生中做過好幾道燉菜。
瑪妮:至于土豆餅——巴巴做這些時,簡直是一流。我們之前從未吃過那樣好的!
我日記中下面記錄的是:‘每天晚上我們都唱《新生活之歌》。巴巴清楚表明他希望我們立刻服從他的命令。’
鄧:誰寫的《新生活之歌》?巴巴本人嗎?
瑪妮:巴巴給了材料,伽尼把它寫成詩文。最后巴巴加入幾行,刪除一些,又增加一些。就像我的燉菜。他的美妙撥弄使它成為現在的樣子。
后來在旅行中,到貝納勒斯時,我們得到巴巴的一個出乎意料的命令:制作木偶!你知道,很久之前在美拉巴德時我做過一些木偶,并為巴巴上演了一出木偶劇。我記得諾芮娜在演出結束后說:‘如果什么時候你需要一份工作,瑪妮,如果巴巴讓你出去找工作,你應該做的是制作木偶。’我們當時笑笑而已,但新生活中,我們在貝納勒斯時,在那座巨大的宮殿般的房子里,埃瑞奇和美婼一定給你講過那兒,巴巴對我們說:‘你們將制作木偶,因為我們從這里上路之后,你們必須開始掙錢。你們可以通過演木偶劇來掙錢。每當我們停留時,人們可以來觀看。他們會喜歡并且樂意為演出付小費。那也將是一種布施形式。’
于是我們開始做木偶。我做臉和手(用紙和膠水),美婼和其她人做衣服和首飾。
鄧:它們是手動木偶還是繩動木偶?
瑪妮:手動木偶。有一個小木偶是主奎師那,美婼為他做了全部飾品和王冠,美茹和高荷幫助縫制衣服。我們做了那些,我們準備做更多時,巴巴突然放棄了這個主意。你知道,巴巴提議,巴巴取消。
鄧:人們說那本應是上帝做的事情。
另一個聲音:人類提議,上帝取消。
瑪妮:是的,但此處是上帝提議和上帝取消。不管怎樣,12月1日我們來到鹿野苑,那兒離貝納勒斯只有幾英里。我知道美婼已經給你講了我們在那兒的逗留。鹿野苑是佛陀第一次給弟子講道的地方。
鄧:那里還有很多佛事活動嗎?
瑪妮:有一個美麗的佛塔。巴巴帶我們去看了佛塔、遺址和僧院,還有一個寺廟,里面有描述佛陀生活的很美的壁畫。一天早上巴巴讓我在一張紙上寫上所有已知阿瓦塔的名字:瑣羅亞斯德,羅摩,奎師那,佛陀,耶穌,穆罕默德和美赫巴巴——把他們全部寫上——他把紙放在口袋里。我不知道之后發生了什么,但是巴巴把紙放入口袋后,走進遺址的地下通道,后來巴巴和男伴侶們就在那兒一起打坐。埃瑞奇已經給你講過此事。
我們在鹿野苑時,為巴巴所稱作的徒步‘fakriri’(苦行)做準備。男子們身著在貝納勒斯時就開始穿戴的白色長衫和綠色包頭巾,但是因為女子們沒有,巴巴讓我們為自己做了淺藍色羊毛長袍,并給了我們灰色棉布塊做包頭巾。為了示范怎么用包頭巾,巴巴把頭巾系在我頭上。但是后來巴巴放棄了這個主意,我們女子在旅行中沒有實際穿戴包頭巾或長袍。他而是決定我們在徒步苦行的第一天穿紗麗。于是給我們弄到淺藍色的棉布紗麗,我們在第一天,12月12日,穿著它們,于早上7:30出發。
這里我的日記寫著:‘像平常一樣奔忙。納斯和柯哈瑞醫生及其他人站在遠處。我們的長隊出發了,?白馬先行(由鄧肯醫生牽著),后面跟著駱駝車(由拜度駕駛),牛車(由韋希奴駕駛),一頭白色奶牛,兩頭牛犢(其中一頭比較小,經常由尼魯醫生扛在肩上),由公牛拉的篷車(彭度駕駛),兩頭頑固的驢子,之后是一些男伴侶,一段距離后面是巴巴和埃瑞奇(他們所有人都穿戴著白色長袍和綠色包頭巾),再一段距離之后是我們四個身穿藍色棉布紗麗的女子(我們只在第一天穿這個)。’
我們一定構成了一副美麗的畫面,除了獲準可以站在遠處的納斯和柯哈瑞醫生(他們給了我們所有那些動物)等人之外,當這個獨特的隊伍經過時,只有帕椎在那兒。他奉巴巴之命從阿美納伽來送篷車,沒有跟巴巴會面。帕椎被告知不可拍照,不可講話,只可在隊列經過時呆在遠處。
后來帕椎對我們說,那個令人難忘的場面銘刻在他的腦海中。他說:‘你們不會知道,因為你們身處其中,但它確實是超凡脫俗,是映入我眼簾的最不可思議的場面,當時天剛蒙蒙亮,我靜靜地望著長隊經過。’
我們的新生活駱駝在脖子上掛著個可愛的波斯銀鈴——現在阿婁巴在傍晚用這只大鈴鐺,提醒你們快六點鐘了,是離開美拉扎德的時候了。駝鈴在哈菲茲的詩文中被提到過,巴巴非常喜愛這位至師的詩歌。商隊的領頭駱駝戴的鈴鐺象征著前進。鈴聲提醒在綠洲中停留而不愿再次上路進沙漠的商隊:‘繼續走。這不是你們的目的地,前進,前進!’
我們的駱駝車拉著動物的食物——干草、飼料、應有盡有。男子們會在清晨三點之前起床,首先照料動物。我們從遠處借著他們的煤油燈光看見男伴侶們切飼料,喂公牛、奶牛、驢子和駱駝,之后才能給自己做茶。有時他們在艱苦跋涉之前只夠時間做事,于是他們只好不喝茶水就上路。
一天當我們的隊伍停在路邊時,拜度離開駱駝車,走過去跟其他一些伴侶說話。不一會兒,一群高興的孩子圍著車,欣賞著駱駝。接下來發生了什么我們不知道,只見駱駝受驚跑開。它沿著街道跑,鈴鐺叮當響著,車在后面沖撞,拜度大喊著追趕,孩子們在后面賽跑。鎮上好奇的人們也加入追趕。每個人都在奔跑喊叫,不過,拜度最終設法追上駱駝,哄他回到巴巴和我們等待的地方。
此類事情貫穿了新生活的長途跋涉。不管我們在哪兒停留過夜,經常是在村莊或小鎮的郊外,一般在芒果園里,有時在破舊不堪的屋棚下,甚至在田野井邊露天,消息會飛快傳到村里說有一隊奇怪的朝圣者在附近露營。因此在整天精疲力盡跋涉之后,甚至在安頓好之前,幾乎全村的人都會跑來看我們。婦女們會聚集在我們女子的地點,男子們會圍在男伴侶那兒。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。如此奇怪的一行男子、女子和車輛隨從:一輛不同于那里常見樣式的駱駝車;一輛由一頭英國公牛和一頭印度公牛拉的牛車;一輛貌似汽車卻由公牛拉的篷車;男子和女子看上去很不同于通常徒步朝圣的那類人;最主要的還有巴巴。顯然他是這隊人的首領,且十分與眾不同。
我們疲勞地在路上走,一英里接著一英里,有時途經村莊或城鎮,或在偏僻漫長的鄉間路上,過路人一般不怎么被隊伍中穿戴長袍和包頭巾的其他人吸引(印度人對人們的穿著方式是寬容的),但是當他們的眼睛落在巴巴身上時,他們會停止聊天,靜止不動,只是看著巴巴經過,然后轉身目送,直到他走出視線。
鄧:巴巴總是注意力的焦點嗎?
瑪妮:是的,當然是巴巴。即使在早些年間乘火車旅行時,我們就知道會發生這個——巴巴戴著墨鏡圍著頭巾以防被認出。在擁擠得難以置信的火車站臺,每個人都沖向剛進站的火車,推著喊著,抱著包裹和嬰兒,有些人看見巴巴,立刻呆若木雞。巴巴迅速走過之后,他們的瘋狂奔跑才會再次開始。
讓我講一件趣事來說明我們是多么容易陷入自我。在新生活的跋涉中,一次在印度北方,篷車在前,我們女子跟在后面走。你知道,篷車只供我們四個人夜里睡覺用。這一次有一輛空牛車經過我們,只有一個車夫。他看見我們四個人走路,就對美茹和我說:‘你們何不坐我的車呢?’我們(我認為)頗為高尚地說:‘噢不,不用了,非常感謝您,但我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。你看,我們去哈德瓦步行朝圣,我們必須走路去,所以不能坐牛車或其它車。我們必須步行。’這個人顯然被感動了——他恭敬地向我們鞠躬,我們也鞠躬還禮。
這個人和他的牛車離開不到五分鐘,就聽見巴巴的拍掌聲,他指示讓我們女子們上篷車。上篷車?我們感到驚訝,但那是巴巴讓我們做的,于是我們照辦,這很讓人興奮。美茹和我坐在座位上,拉開小車窗的窗簾,伸出頭。不必走路卻能看見一切真好玩。
過了一會兒篷車經過一輛牛車。駕車人碰巧扭頭瞧見我們,我想:‘他看上去面熟。’他的眼中有一種很受傷與責備的神情,像是受了騙。我們突然想起了——那是幾分鐘前讓我們搭車的好心人。太遲了,美茹和我把頭縮回,感到十分羞恥。
嗯,巴巴就是那樣挫敗我們的自我的。此事剛過幾分鐘,巴巴傳話:‘女子下車走路。’我們走著路,但再也不炫耀了。
1950年1月1日,我們在北印度的莫拉德巴德。我那天的日記寫到:‘從今天起,每天早晨伴侶們要念四種語言的禱文:瑣羅亞斯德教,印度教,基督教,穆罕默德教。被選的四個象征著所有的宗教。’這持續了一段時期,然后停下了。
在德拉敦郊外的曼吉瑞村,因巴巴在新生活期間住在那兒,現在被正式命名為美赫村,有一段時間它是基地,巴巴同一些男子從那里去聯系圣徒和求道者。我(1950年)4月3日的那頁日記寫到:‘今天巴巴結束了對圣徒的工作,他通過彎腰碰觸每個人的腳來聯系他們。就這樣他一天中頂禮了三千人,用了約十一個小時。’
鄧:巴巴頂禮了三千人?那么多?
瑪妮:是的,一天三千人,彎腰碰觸每個人的腳,用他的手碰觸他們的腳,然后用手指碰觸他自己的額頭。
鄧:瑪妮,孟買那個優秀醫生叫什么名字?也就是在巴巴晚年醫治巴巴頸部的那個神經學專家?
瑪妮:金德。羅摩.金德醫生(Dr.Ram?Ginde)。
鄧:我記得跟金德醫生交談過,當時巴巴仍在肉身。我很擔心巴巴頸部的疼痛,想知道是不是痛風病。它跟你剛才讀的內容有關系——巴巴一天頂禮三千次。羅摩.金德說:‘不是,鄧。我很仔細地看過巴巴的X光照片,我可以看出那實際上是由于他頸部的一對脊椎骨磨損,這致使脊髓穿過的通道變窄。’他還說:‘這種磨損我只能歸因于巴巴這么多年向那么多的人頂禮,實際上磨損了那些骨頭,從而使脊髓穿過的通道變窄。’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這個數目,三千個。這就不奇怪了。這不可思議。
瑪妮:那是在哈德瓦舉行的大法會期間,大群的圣徒為了這個偉大日子涌到恒河邊集會。巴巴和男伴侶們從曼吉瑞村到一個叫做莫提徹的地方,埃瑞奇給你講過,并在那里住一些天。莫提徹的天氣寒冷多風。每天早晨四點鐘巴巴會從莫提徹走到哈德瓦,到阿克達斯(akhadas,圣徒們的營地)聯系圣徒。埃瑞奇跟他一起去。巴巴對我們說,雖然他向成千上萬人頂禮,但只有幾個人實際上令他滿意,他會對我們講關于他們的事情。
4月3日是這次特別的圣徒工作的最后一天。我的日記記載:‘他走回莫提徹,精疲力竭。’4月4日巴巴返回曼吉瑞村。我在日記中寫到:‘巴巴完全精疲力盡——他渾身疼痛發燒。他已經完成了在那里的工作,總共聯系(頂禮)了一萬多個圣徒。’
4月12日是大法會日,巴巴帶領我們所有人跟他一起去哈德瓦見證。無法描述我們所見到的——難以置信的眾多人,來自全印度的數百萬印度教徒匯集在恒河岸邊,在圣水中沐浴以洗刷罪孽,祈禱,搖鈴,吟誦,歌唱。
我們女子跟巴巴一起從一家旅館(果爾旅館,Goel’s?Hotel)的露臺上觀看。旅館主人讓我們使用他的露臺,但是他不可以見巴巴。只是請他保證巴巴和我們在露臺上不受打擾。河就在我們前面,所有的人都圍著它,密不透風的人眾,載著鮮花和油燈的微小葉舟順流而下。整個場面多彩喧鬧,同時又極其簡單和激動人心。令我們失望的是,我們只能看到一點點圣徒和大象等盛裝游行,雖然它們在離我們不遠處經過。
可憐的男伴侶們辛苦地站在我們下方的人群中,簡直是忍無可忍。每當需要照看什么時,巴巴都會傳信給他們。巴巴對露臺上的一些安排不滿意。我不記得確切原因了,但巴巴生氣了。他傳話給旅館老板果爾說他不高興。這意味著發生了什么事情,影響了他當時所做的工作。但是不一會兒,像通常一樣,整個問題煙消云散,一切恢復平靜。只有巴巴能做到這個。
鄧:他消除了情緒。
瑪妮:是的,整件事結束了。但是當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時,巴巴跟我們女子走在一起,我們看見老板靜靜地站在遠處。巴巴讓我去告訴他,巴巴對他和他提供的服務極為滿意,巴巴還請他原諒曾對他生氣。
我去傳的話。傳遞巴巴的道歉本身都很困難——至少可以這么說。但是當我看到旅館主人的臉時,則變得更加困難了。他站在那兒,雙手合十,迫切地等待著巴巴的話。我迅速開始說我必須說的話,但是當我說到道歉部分時,那個可憐的人只是低下頭不抬眼。他做不到。他顯然非常謙卑和羞愧,我肯定他一定想找個地縫鉆進去。
鄧:瑪妮,有個技術細節。巴巴像這樣跟你們一起走時,突然想對旅館老板有話說,他會打手勢還是隨時帶著字母板?
瑪妮:我記得那時巴巴使用字母板。
鄧:比如,他走出旅館,給你這個信息時,他會停下并拿出字母板嗎?
瑪妮:通常我們為他帶著字母板,雖然他用過后有時會自己拿一會兒。
鄧:所以他立刻就能拿到?
瑪妮:是的。他既通過字母板交流,也用手勢——如果信息簡短或某人善于翻譯的話。
鄧:所以那時他已經在為后來完全用手勢交流打基礎了?
瑪妮:是的,他兩種方式都用。再回到我的日記,它寫著:‘5月1日,巴巴和男子們穿戴長袍和包頭巾,一起去德拉敦的三個愛者家中乞討施舍。從今天起‘新計劃’開始,所有人都在B組。’也就是說,所有的人必須工作掙錢,比如制作精練黃油去賣。
鄧:聽起來像是個足球隊,有不同的編碼,你們得使用各種打法。
瑪妮:‘為了慶祝新計劃的開始,大家被款待一道甜點,**并且**男子們終于理了發。5月22日,巴巴去德里一周,為在那里制作精練奶油的可憐的滿德里們做出新計劃,他們在沸騰的溫度下和饑餓節食中做這一切。’
鄧:鄧肯是不是也在其中?
瑪妮:是的,他是!巴巴不在的時候我們女子縫紉并做了一些東西賣,作為我們的賺錢和貢獻部分。我們做貼花和可愛的床罩。我們兩個月的工作掙了兩百盧比的利潤。我們做出的成品很漂亮,但不得不賣掉它們。
7月25日我們在薩塔拉。‘巴巴說這是新生活最重要的日子。他向東西方的所有門徒和愛者發出個人的信息和問候。他全天禁食,只喝水。上午是祈禱活動,朗誦《博伽梵歌》(Bhagavad?Gita)的英譯本;由孟買的卡瓦利歌手唱《新生活之歌》。下午巴巴做瘋子和瑪司特工作,他們被找到并帶來,巴巴給他們剃須、洗澡和穿衣。’
鄧:巴巴說過為什么選擇7月25日嗎?它有特殊意義嗎?
瑪妮:據我所知沒有。但現在它當然有意義。之后,‘7月27日,巴巴兩次乞討施舍,一次在一個印度教徒家,一次在一個穆斯林教徒家。’
哦,鄧,我的記錄就這些了。但是我可以談一些看法,比如巴巴對動物們做的工作。我們跟巴巴一起生活的整個期間,顯然巴巴不僅在所有的層面上工作,而且對整個造物界和所有的生物工作,并且通過他們工作。想一想巴巴養的所有那些寵物,我們在跟隨巴巴的多年間,曾擁有并照看的所有鳥類和動物。在我1938年的日記中寫著:‘晚上巴巴回房間休息之前,會和我們一起巡視每只寵物,每個籠子,每個圍欄,養寵物的每個地方。’想像一下,他就寢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訪問每一只寵物!那時我們住在美拉巴德山上。跟隨巴巴乘藍車在全印度旅行時,我們跟巴巴一起的‘觀光’總是包括參觀當地的動物園。這是巴巴通過動物園里的集體標本,聯系動物世界的方式。
無疑這些外出不僅是為了讓我們享受,而是為了他的工作。巴巴很少給我們時間來欣賞動物。他經常走得極快,我們要小跑才跟上他。用這個辦法,也使我們的注意力不從他身上溜走。
我的看法是他以人身在此,不僅為我們也為動物、鳥類和所有的生物。同樣在新生活中,伴隨巴巴的有男子和女子,還包括動物們。當那個階段結束后,有些動物被送人,有些被賣掉,有些被拍賣,有些被留下一段時間。
鄧:這聽起來幾乎像是一個行走的‘諾亞方舟’。
瑪妮:難道不是嗎?
鄧:瑪妮,動物和鳥類對巴巴有什么反應?
瑪妮:你是指新生活中?
鄧:不,一般來說。
瑪妮:哦,它們非常敏于接受巴巴傾注給它們的愛。巴巴對寵物的照顧很講究,不管它們出了什么事,我們都會被訓斥。巴巴喜愛喂鳥和動物——事實上把它們喂得過飽。即使我們已喂過它們,它們一看見巴巴也會叫著乞食。他會責備我們:‘你們沒好好照顧動物。瞧,它們都餓著。必須喂飽它們。再拿些來。’之后他會再喂它們,它們會狼吞虎咽地吃光,好像一直在挨餓似的!
鄧:瑪妮,你對新生活的總體感覺是什么?艱苦嗎?
瑪妮:嗯,不只是身體的艱苦。有那方面的。不僅是艱苦生活,還有嚴格服從方面。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覺,以免違背巴巴為新生活規定的條件。
鄧:巴巴要求你們特別關注,是嗎?
瑪妮:是的,不是對個人的關注,而是全神貫注地執行巴巴給我們的任務。有時我們會犯錯,甚至意識不到在做錯事。但是巴巴會在那兒知道并提醒我們。
鄧:他比新生活之前更強調一絲不茍的服從嗎?
瑪妮:是的,它是之前的加速,擴大。比如我們在貝爾高姆時,巴巴命令:‘不要閱讀任何東西。’嗯,那不是簡單意味著我們不能讀書或偵探故事——它意味著我們不能讀任何東西,甚至是攤開的報紙。你知道,在印度家庭中大多用報紙做各種東西的便利包裝紙。為了幫助我們避免不慎讀到用于包裝或生火的報紙,韋希奴從舊貨店弄來外語舊報紙,我們都不知道在印度印刷那些不尋常的語言!我想它們是保加利亞語,匈牙利語或捷克斯洛伐克語之類的。這樣我們就放心了,知道我們不必竭力避免瞟見我們的包裝報紙。
鄧:是的,即使是有告示的汽車路過,你們也必須避免讀它。
瑪妮:對,就像走鋼絲。
鄧:我想這會給人造成巨大的壓力。神經會疲憊嗎?
瑪妮:是的,會隨時隨地發生。另一方面,因為巴巴,巴巴跟我們在一起,巴巴在場,這使情況完全不同。
鄧:這么說他給了你們巨大的挑戰,但他又支撐著你們迎接挑戰?
瑪妮:正是如此。如我所言,如果巴巴用一只手拿錘子敲打,那么他會用另一只手支撐你。他在對你做工作時,不會留下你無支撐。如果要打碎果殼,他則把果殼握在手里。
鄧:你知道,這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,因為在瘋狂地愛上巴巴一段時期之后,一個人會突然開始面對不僅是生活中的一些舊問題,甚至還有一些更復雜的新問題。那時很多人感到:‘噢,我一定是沒有抓牢巴巴。這怎么能發生在我身上?我的態度一定是有問題。’他們感到極為苦惱。
瑪妮:不。巴巴只是剛剛開始工作。‘蜜月’結束,工作認真地開始。
鄧:真正的工作才開始,如你所說,重要的一點是巴巴在支撐著一個人,只要他懷有信心并抓緊巴巴的衣邊(完全地信任服從他)。
瑪妮:這個毫無疑問。你認為我們能經歷那一切并臣服他,是我們自己的功勞?我們也努力了,沒錯,但我們能完全臣服巴巴,不是我們自己的任何功勞。不是。那是因為**他**的幫助和支撐。是**他的**愛——說到底是這樣——?是巴巴的愛和慈悲使這一切成為可能,甚至使我們愛他成為可能。他讓我們感到我們在給予,我們在服務,我們在愛。他甚至會表現得虛弱,以便讓我們感到我們在支撐他。
例如:在那最后的一個月(69年1月),巴巴坐在椅子上(在美拉扎德的滿德里大廳),看上去疲憊虛弱。他示意該回房間了,埃瑞奇和弗朗西斯躍起,每人給巴巴一只手幫他從椅子中站起來。當時我在那兒。巴巴握著他們的手,他們準備把他拉起來,這時他輕輕地拉了一下,把他們拉向他。他們倆人立刻開始向前跌,竭盡全力不往巴巴身上倒。而一秒鐘之前巴巴卻顯得如此虛弱!站穩之后,弗朗西斯叫道:‘巴巴,您很強壯!’巴巴眼睛閃爍,點頭說:‘但沒關系,幫我起來。’并再次變得虛弱。
像他做的每件事一樣,那也是他的慈悲的體現,給我們機會用我們的小小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愛。一直以來是巴巴在支撐并緊抓著我們,是他愛我們,是他容忍我們。現在我會這么說了,但是最初我們也曾是生硬頑固的材料。現在我們希望那時更靈活些。我們學到了教訓,我們成熟了——在某種程度上——但是一個人永遠不能成熟到足以配得巴巴的愛,絕不會。
鄧:因此對個人的真正挑戰是在艱難時期堅持下去。真正的挑戰是尋找并發現,實際上是巴巴的愛在那兒支撐著我們,并且靠巴巴的愛解決必要的問題——在消除業相時所涉及的問題。
瑪妮:沒有其它辦法。一旦你在巴巴的網中,他是不會讓你避免經歷那個的。有人會擔心自己迷失,但是我們必須記住,當我們緊握巴巴的衣邊時,他在握著我們的手。巴巴從不讓事情容易,但他總是使之可能。當我們完全依靠他時,他則美妙地使之可能。當你不再為了自我,而是為了巴巴的那一刻,那就會發生。他的愛會把你武裝起來去迎接生活的挑戰,正如你為了讓他高興也會那么做。
鄧:所以你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?
瑪妮:是的,看到巴巴對我們做的某件事高興,絕對是天堂。當我們在某個方面使他不快時……
鄧:絕對是地獄。瑪妮,新生活中你感到最艱難的是什么?埃瑞奇說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快樂對他來說是最困難的。
瑪妮:是的,當然,保持快樂意味著我們不能抱怨,不能難過或憂愁滿面。對男子們最艱巨。我們也要那么做,但是男子更不容易。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小影院停留過夜。我們女子睡在舞臺上,在電影屏幕后面。有一盞燈亮著,我在屏幕上做手影,做成兔子等等。巴巴和男子們在一起,在我們的視線外,但我們可以聽到埃瑞奇的聲音,他正翻譯巴巴對他們的談話。
我們聽到巴巴說的其中一件事是:‘在新生活中你們必須做自己面孔的主人,無論發生什么。’這意味著你永遠不能讓臉上泄漏出任何可能的不快情緒。然而,僅僅戴著面具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,因為巴巴會把你心里可能升起的最微小情緒波動激發出來。他會發現并把它帶出來。
另一個聲音:即使你感到不快樂也必須快樂嗎?
瑪妮:快樂不意味著你必須微笑著走來走去。如果你在錯誤的時間那么做,則同樣糟糕,巴巴會訓斥:‘你為什么咧嘴笑?’我們至今也沒有真正理解快樂、幸福這些詞的含義。快樂可以是沉默的——快樂可以是絕對的沉默本身。幸福是一種平靜,不只是唱歌跳舞。它仍然是尚未發展完善的東西,也許巴巴把它鑄入我們。
另一個聲音:像埃瑞奇說的,有時你會感到生氣。但如果那時巴巴面對著你,你怎么能在生氣的同時感到快樂呢?
瑪妮:你去問巴巴怎么能做到!
鄧:在生氣上面掛個簾子。別管它。走過它。在巴巴的《神曰》補編里有一部分談忘卻。其中他描述了靈性求道者需要培養忘卻技術的絕對必要性。
瑪妮:忘掉你自己。或者說控制。1940年我們跟巴巴在班加羅爾時,巴巴提到過這個。伊麗莎白、諾芮娜、娜丁、吉蒂、瑪格麗特和所有的西方女子也在那兒。發生了某件事——有人因感到生氣而悔恨——巴巴說:‘假如你不會生氣,有什么好處?我不希望**石頭**圍在我身邊——那怎么能幫助我的工作呢?但是,當你感到惱怒時,控制它——那是關鍵!’
另一個聲音:聽上去好像巴巴開啟了這個快樂新感官,怒氣中的能量被直接導向快樂。是那樣的嗎?
瑪妮:我不知道,不過,有時巴巴不希望我們顯得快樂,有時巴巴會對我們某個人說:‘我不舒服,而你們卻這么高興!’我們必須學著培養隨時覺察到巴巴的喜好。那不是可以貼上標簽的東西,或像太妃糖一樣可切成方塊。它是很微妙的,像流動的水,你必須了解它的感覺,把它握在手里,不讓它從你的指縫中溜掉——如果你能做到,你就是有福的人。
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。跟巴巴在一起沒有妥協。你可以做你明知會讓他不快的事情,并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。有一千種理由會來站在你面前,舉手幫助你。但那沒什么益處——你只是在愚弄你自己。正如巴巴所說,重要的不是你是好還是壞,重要的是你是他的,你已經將自己臣服于他。‘把你的一切交給我。之后它便是我的,它不再是你的。’觀看巴巴對我們的弱點且利用我們的弱點做工作,把我們的債務轉化成債權,是很美妙的事情。
鄧:瑪妮,你提到,我記得埃瑞奇也提到,在巴巴離開肉身的最后日子里,他雖然健康狀況很差,仍然每天至少來滿德里大廳一次,像多年來一樣和他們坐在一起。
瑪妮:直到1月中旬他還來滿德里大廳。
鄧:1月中旬?僅僅他離開肉身的前兩周!
瑪妮:我們記得直到13日——沒錯,幾乎到你的生日那天,1月14日。
鄧:是的,他給我拍了一份生日賀電。很美妙。在這種時候想著做這個。但是他繼續去滿德里大廳,這讓我非常感動。很多人感覺慣例和形式完全是虛假的,但這里有個慣例,有個形式,巴巴堅持到他的肉身能夠堅持的最后時刻,每天來跟滿德里在一起,同他們坐在一起。
瑪妮:看到他的人性怎樣地示現他的神性,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這沒有使他少于神,而使他更是神。一個人必須跟他在一起才能知道這個。
坐在這兒的滿德里大廳對你談這一切,讓我不禁想起巴巴怎樣每天早上都來這兒,在那把椅子上坐下之前,他會在大廳里走一會兒。他來來回回地走,一只手搭著卡卡的胳膊,另一只搭著弗朗西斯或埃瑞奇的。拜度坐在其他滿德里中間,也許對卡卡和其他人在巴巴走路時攙扶他而感到一點嫉妒,他也渴望從巴巴那里得到一點個人關注,巴巴會突然停在拜度面前,摸摸他的下巴。雖然拜度不說一句話,但你也能看得出他心花怒放,因為那個慈愛的接觸,那個適時的愛的表示。雖然巴巴過去和現在都是為了所有的人,但他會用千百種的小方式來使每個人感到他是為了這個人。在印度,每當我們稱呼巴巴時,我們習慣地叫:‘噢,我的巴巴!’而事實上,每個人都可以說‘我的巴巴’,每個人都可以是完全正確的。
譯自《新生活的故事》(Tales?from?the?New?Life,?narrated?by?Eruch,?Mehera,?Mani?and?Meheru,?1976)
翻譯:美赫鋒???????校對:田心
- 簡介
- 每月活動記錄
- 美赫巴巴是誰?
- 怎樣憶念美赫巴巴
- 美赫巴巴答問
- 阿瓦塔的名
- 生平往事
- 美赫巴巴的父母
- 至愛的至愛
- 神圣的戀愛
- 美赫巴巴生平簡介
- 童年與青少年時代
- 面紗是怎樣揭開的
- 老家水井
- 生平四個階段
- 五位至師
- 赫茲拉·巴巴簡
- 納拉延·馬哈拉吉
- 塔俱丁巴巴
- 舍地的賽巴巴
- 烏帕斯尼·馬哈拉吉
- 阿瓦塔
- 阿瓦塔
- 圈子
- 阿瓦塔的圈子
- 當代阿瓦塔的訊息
- 美赫巴巴的睡眠
- 阿瓦塔作為第一個大師
- 阿瓦塔與賽古魯
- 彼得的否認與猶大的背叛
- 七月十日沉默日
- 阿瓦塔的獨特性
- 真正偉大
- 復活節
- 阿瓦塔的受難
- 顯現
- 門徒的寫作過程
- 原始問題的聲音
- 阿瓦塔的聲音
- 最偉大的顯現
- 阿瓦塔的工作
- 宇宙工作三階段
- 宇宙性推進
- 梵天之夜
- 神的工作不是說教
- 七月十日沉默日(重復章節)
- 信心與期待
- 兩則寓言
- 內在體驗階段
- 阿瓦塔的蒙辱
- 他的最后訊息
- 工作
- 蘇非教再定向指導憲章
- 宇宙工作
- 美赫巴巴與蘇非教再定向
- 美婼美赫【作者:戴維·芬斯特】
- 《美婼美赫》序言
- 1特別的孩子
- 2 學生時代
- 3 皇家旅館
- 4 白馬
- 5 托迪瓦拉路
- 6 默文吉
- 7 婚禮安排
- 8 美婼的決定
- 9 新朋友
- 10 戒指與照片
- 11 反對
- 12 美拉巴德
- 13 奎達
- 14 日出之歌
- 15 巴巴的勤務兵
- 16 考驗時期
- 17 沉默
- 18 拉妲
- 19 伊朗尼上校
- 20 修愛院
- 21 托卡的拔河比賽
- 22 鴿屋
- 23 去西方
- 24 神圣戲劇
- 25 瑪妮
- 26 西方人來訪
- 27 上美拉巴德
- 28 他不在時的忙碌時光
- 29 美拉巴德動物園
- 30 血誓
- 31 邁索爾摩耶
- 32 三環馬戲團
- 33 西方人在山上
- 34 船上閉關
- 35 里維埃拉河上的擠奶女
- 36 帝王臨朝
- 37 歸航
- 38 新來者
- 39 盤奇伽尼假期
- 40 白塔高聳
- 41 搖籃曲中道晚安
- 42 藍車旅行
- 43 在路上
- 44 瑣碎的爭執
- 45 球場屋
- 46 十勝節游行
- 47 戰爭工作
- 48 家門口
- 49 命令
- 50 戰時閉關
- 美婼美赫附錄一
- 新生活
- 新生活方案說明
- 美赫巴巴的新生活
- 什么是新生活?
- 新生活的意義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行乞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權威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危機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巴巴知道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情緒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特殊窮人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身份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美婼回憶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瑪妮回憶
- 培訓階段
- 末那乃息
- 完美者
- 自然——阿瓦塔的標記
- 金錢——完美的經濟學家
- 完人
- 完美的標記
- 辨喜論靈性導師
- 行道者【作者:威廉·鄧肯】
- 序言
- 關于瑪司特【作者:美赫巴巴】
- 瑪司特對人類的功用
- 靈性高級靈魂
- 靈性高級靈魂及瑪司特類型
- 五個最愛之說明
- 穆罕默德
- 恰提巴巴
- 卡瑞姆巴巴
- 阿里·夏
- 恰恰
- 瘋人埃舍
- 七個瑪司特埃舍之說明
- 阿杰梅爾
- 賈巴爾普爾
- 班加羅爾
- 美拉巴德
- 蘭契
- 馬哈巴里什沃
- 薩塔拉
- 那些見證者
- 美赫巴巴的瑪司特之旅
- 旅行示意圖、地名及數據
- 附錄說明
- 附錄(一)
- 附錄(二)
- 附錄(三)
- 附錄(四)
- 附錄(五)
- 補充附錄
- 最新消息
- 增補
- 再增補(一)
- 再增補(二)
- 再增補(三)
- 再增補:聯系匯總
- 作者簡介及后記
- 達善時刻【作者:美赫巴巴】
- 意義與體驗
- 真達善
- 真正生活
- 誠實
- 時間
- 唯一障礙
- 只要愛
- 真答案
- 救治良藥
- 雙重角色
- 愛的禮物
- 自我性質
- 緊抓衣邊
- 無限珍寶
- 完全忠于我
- 神圣戲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