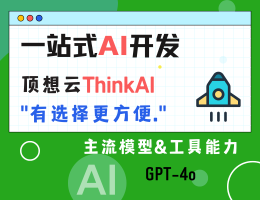美赫巴巴曾解釋,在整個印度*,除了庫特博之外,還有三位第七層面者——兩位瑪居卜,一位吉萬莫克塔*——而恰恰,是兩位偉大的瑪居卜之一。這無疑是個諷刺,一位淹沒于神者,對我們來說,本質上應該始終是個謎;但是,當一個人試圖了解這位帕坦老人時,他的思想會被這樣的愿景激發:即去探尋并贏得,在恰恰飽受摧殘的骯臟身體深處埋藏著的無限喜樂之圣杯。一個人的智力可能會反抗,但直覺之耳語會在內心的走廊上回響:即恰恰真正已經登峰造極,而我們依舊在僵化思維習慣的霧谷中摸索。對于一個熟悉蘇非或吠檀多學識的人,或者對于少數基督教神秘主義者,這種靈魂的存在,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;但對于一個不精通這些教導的人來說,這個問題困難重重。對這些讀者,我只能建議他,應該重新閱讀巴巴在第一章的解釋,其中闡明了為何一個像恰恰這樣融入于神的靈魂,對世間環境完全漠不關心。?
[注:此處印度指現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。另一位瑪居卜是巴特的巴巴·夏哈卜丁,吉萬莫克塔是亞德吉里的伊希瓦·達如·斯瓦米,參閱附錄。]
有關恰恰歷史的以下筆記是拜度講述的,他從阿杰梅爾的諸多人士搜集得來。恰恰是帕坦人,真名是奴爾·阿里·夏,許多年前從白沙瓦附近的家鄉來到阿杰梅爾。他的妻子和兒子仍在世,兒子有時會從白沙瓦來,探望年邁的父親。恰恰曾是一位“哈菲茲”,即能熟背古蘭經者,來阿杰梅爾教授阿拉伯語。到后不久,他去了著名的克瓦伽·姆伊奴丁·齊西提的圣陵,并似乎感到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居住那里。有十二年,他一直待在克瓦伽·薩赫伯圣陵里的索拉-卡姆巴(solah khamba)墓地,期間他的身上似乎發生了什么,因為從那以后他成了瑪居卜。十二年后,他從圣陵出來,在一個地方坐了六年。之后的一年,他去了阿杰梅爾后面高山上的塔拉加爾大古堡。
從塔拉加爾,他往南大約300英里,來到印多爾。有個奇異而難以置信的故事:他在那里死去,并被埋葬。在印多爾,他被叫作甘賈巴巴(ganja指禿頂)。據說他死后一年左右,一些民眾從印多爾前往阿杰梅爾,參加克瓦伽·薩赫伯圣陵的年慶活動,期間他們震驚地發現:恰恰,印多爾人稱呼的甘賈巴巴,依然活著,坐在圣陵旁的水龍頭邊上。據說,他們把其他印多爾人叫來,這些人同樣認識甘賈巴巴,曾見證他死去被埋葬,他們也確認了他的身份。這個死而復生的奇聞隨后開始廣為流傳,恰恰名聲大振。故事是不是純屬虛構,我不知道,無疑讀者將根據自己的傾向,接受或否認之。至少這是個例子,說明圍繞一個像恰恰這樣的人物可能興起的那種傳奇故事。在水龍頭旁邊坐了幾年后,恰恰最終搬到一間小棚屋,過去16至18年來,一直住在里面。
巴巴與恰恰之間的聯系始于1939年2月。1938年12月,巴巴率領一批東西方弟子,駕車外出旅行。從美拉巴德啟程,他們先去海得拉巴,其坐落在德干高原心臟地帶的新月形花崗巖群山之間,從那里他們加速北上,經過中部省邦的賈巴爾普爾和森林地帶,前往貝拿勒斯、阿格拉、馬圖拉和德里。參觀過這些宏偉的城市(其城墻曾被無數軍隊的箭矛槍炮摧殘),之后他們調轉往西,穿越拉吉普塔納的沙質平原,來到阿杰梅爾。阿杰梅爾依偎在干旱的阿拉瓦利群山中,是克瓦伽·姆伊奴丁·齊西提之寓所,他的圣陵聞名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。
他們抵達后過了幾天,巴巴開始聯系許多瑪司特,并建立一個小型瑪司特埃舍。此埃舍在其他地方有描寫,故我在下文所述,將僅限于巴巴對恰恰的工作。
當時,恰恰住在克瓦伽·薩赫伯的圣陵附近,那間虱蚤滋生的骯亂小棚屋里,從未聽說他離開過。一個侍者照顧他的需要,恰恰自身臟得難以置信。他戴著舊帽,身上衣服散發異味,被變質的茶及腐食的碎屑,浸透弄臟。之所以叫他恰恰,是因為他嗜好喝茶(cha),每當他想喝茶,經常喊道“茶,茶。”大量的茶沒有被咽下,而是被潑在他的衣服上,并且——天曉得怎么回事——潑在他的帽上,久而久之變質的茶和糖結成硬殼,粘著頭皮揭不掉。
卡卡被派去帶恰恰來巴巴這里,也許正如卡瑞姆巴巴的事例,他被賦予內在鑰匙以開啟恰恰的意識之門。不管怎樣,卡卡把恰恰帶到巴巴的住所,令本地人大為驚奇,因為之前從未有人做到這點,自從許多年前恰恰來到阿杰梅爾,從未見他應任何人的要求去過任何地方。
恰恰一帶到住所,巴巴和滿德里就準備給他洗澡,但這樣做之前,必須先用剪刀將他的帽子和衣服剪掉,因為如我們所知,衣帽由于茶、食物和污垢而變硬、粘在身上,要去除他的衣帽別無他法。
那天,恰恰經歷了近30年來首次洗澡的獨特經驗,事實上,這也成為他的最后一次洗澡,因為即使1947年他逗留薩塔拉期間,都堅決拒絕洗澡,而以前或之后,相信都不會有人給他洗澡。這次洗澡后,給他穿上新卡夫尼。他隨后向巴巴要了一道特別的素菜和粟米面包。食物送來后,巴巴親手喂他。飯后,恰恰要叫馬車,車被叫來,他上了馬車,叫巴巴坐他身邊,二人一道出發。恰恰簡短地吩咐馬車夫,把他們送到塔拉加爾。不過巴巴似乎不想和恰恰一直乘到該古堡,只把恰恰送到他的棚屋,把他留在那里。
初次聯系后,有兩周左右,巴巴每晚凌晨3點半起來,經過昏暗無人的街道,到恰恰的棚屋,單獨同恰恰坐一個小時。這些夜間訪問實屬不得已,因為白天群眾太多,不便私下聯系。
從1939年2月的這些最初會面到1947年恰恰造訪薩塔拉,期間巴巴多次去看望恰恰,單獨同他靜坐,讀者想了解各次會面的日期,可參閱附錄的阿杰梅爾部分。
具有批判思維的的讀者可能會想知道,巴巴為何不安排把恰恰的臟亂不堪棚屋打掃干凈,或者讓他搬到更有益健康的環境。實際上,巴巴曾多次命令滿德里,將他的屋子打掃并布置一番,可恰恰駁回所有這些努力,命令他們走人。1947年恰恰在薩塔拉時,他貌似執著于臟衣服,同樣的態度顯而易見——實際上反抗把他衣服脫掉的嘗試——那時巴巴解釋說,瑪司特穿的衣服和身邊的零碎物品,有著某種內在意義,為此原因,他們才固執地抓住不放。
1942年7月,巴巴訪問阿杰梅爾,聯系恰恰和另兩個瑪司特中的一個,當時做了精心安排,給恰恰充足供應茶。一如既往,巴巴后半夜去與恰恰靜坐,那時的街上沒有白天的擁擠人群經過他的棚屋。一只可容納上百杯茶的大茶炊——有龍頭取茶,燒著木炭使茶保持滾燙——被擺在他的房間一隅。把茶炊擺在近處的目的是,如果恰恰需要茶(他通常每隔幾分鐘就要),巴巴不必離屋,可以立刻倒一杯茶,因為立即回應了恰恰對茶的迫切要求,他的心情會保持最佳狀態。在本章早些對穆罕默德的記述中,我已經提到,巴巴強調他必須滿足瑪司特最微小的心血來潮,假如未做到這點,瑪司特一旦感到他的意愿受挫,一怒之下會損害友好關系。在這方面,瑪司特就像兒童,有著極不合邏輯的喜好,若這些喜好受阻撓,就會變得惱火。
然而這次,恰恰似乎存心要跟那只醒目地立在房間一隅的茶炊作對,推翻了所有預測,整整兩小時聯系期間,他只要了兩三次茶。因此,巴巴做完靜默工作后,出來時下令,將剩余的九十七或九十八杯茶,免費贈送幾個晚到的朝圣者,他們仍在進出克瓦伽·姆伊奴丁·齊西提的圣陵。
另一次訪問阿杰梅爾,巴巴和男子們在拂曉前一兩小時,單獨前往恰恰的棚屋。棚屋是一間小室,高約五英尺,上方是另一間小室,墻上有幾級臺階,故不會太困難,就可以上下攀爬。上方小室住著一人,他相當于恰恰的侍者。他會喂恰恰,大體上照顧其微薄的需要,那些尊敬恰恰的信眾會給他小費。巴巴每次過去,會給此人5盧比小費,故他會很樂意地期待著巴巴來訪。這天凌晨,侍者在上方的小室睡得正香,但是,將其耳朵聽覺與以往小費的愉快記憶聯系一起的某種反射,使他突然醒來,聽到下方巴巴弟子們的說話聲。他急欲下來見巴巴,在半醒狀態下,忘了他的小室地面與下方街道路面的距離近五英尺,一下躍出門外,倒栽蔥摔在街道上。幸運的是他沒有受傷,這一幕令巴巴和男子們哈哈大笑。他得到了5盧比!
1946年7月,巴巴再度訪問阿杰梅爾,卡卡講到當時恰恰表現出心情十分愉快。巴巴一手拿杯碟,另一手提著滿滿一壺熱茶,進入他的房間。恰恰卻拒絕了茶,要羊肉和面餅(他是帕坦種姓,帕坦人愛食羊肉)。送來肉和餅后,給他,他又要了三次。之后巴巴同他坐了近一個半小時,能聽到恰恰一直笑個不停。
巴巴的滿德里,從晚餐至就寢之間的愉快時光里,會閑坐著,談論白天的事,或者隨便閑聊,話題常轉向巴巴和他的瑪司特工作。這些時候,大家普遍承認,卡卡的突出功績是1940年把加爾各答的卡瑞姆巴巴帶到巴巴這里。拜度的圓滿工作,無疑是1947年6月將恰恰從阿杰梅爾一路帶到薩塔拉,這個簡直奇跡般的成就。
也許根本不可能讓讀者了解,一個像恰恰這樣的瑪居卜的那種任性頑固,或者你想實話實說,即那種十足的頑固不化。就他們與世界及其普通民眾的關系而言,這樣的人毫不在意任何人。他們表現出要么對人類懷有一種精神上的輕視,要么如同一個新生兒般,只是根本不在乎人類;只有當他們感到一股更偉大的靈性力量——比如巴巴——的牽拉,才偶爾會依從巴巴滿德里的請求。這方面,埃利奇布爾的古拉卜巴巴——1939年被卡卡帶到賈巴爾普爾的埃舍——非常有趣,因為古拉卜巴巴的話表明,他感到巴巴在拉他,他作了反抗,卻被迫來到巴巴身邊,盡管他的一部分個性與之抗爭。
1947年5月底,巴巴一行從馬哈巴里什沃遷至薩塔拉。巴巴一到,就開始籌建瑪司特埃舍。拜度被派往阿杰梅爾,遵令爭取把恰恰帶到薩塔拉。
到5月底,印度大地上的風景被曬焦、令人生畏,干旱的土壤似乎渴望著未來6月季風雨的滋潤。當拜度前往阿杰梅爾,穿越途中沉悶的風景時,讀者可以想象,隨著他越來越接近恰恰的住處,反復縈繞在他腦際的希望與懷疑思緒。他于5月末周抵達阿杰梅爾。克瓦伽·薩赫伯的年慶活動,正進行得如火如荼,天氣酷熱,供水不足,前來拜謁此重要圣陵的人群熙熙攘攘。
有三四天,拜度頻繁拜訪恰恰,雖百般嘗試勸他走,皆徒勞無果。5月31日夜晚,他又過去,現在他頗為消沉,相信無望完成任務。恰恰叫他取些米飯、羊肉及凝乳,并且喂他。拜度照做,之后恰恰又要一些。要求獲得滿足,他最后吩咐,給他一點冰水。之后拜度突發靈感,集結他的說服力,直接對恰恰的頑固發動最后的正面進攻,并攥住恰恰的手,吩咐他跟他一起走。令拜度驚訝的是,恰恰立刻起身,從地上撿起一塊臟毯,跟他走到街上。二人坐上一輛馬車,立刻前往火車站。
除非一個人見過印度的宗教集會,否則幾乎不可能想象,形形色色的朝圣人群懷著愉快放松的心情四處游逛的場面。如果他是人群中的一員,不忙于特殊任務,觀察這些樸實的民眾蠻有意思。然而拜度,有著明確目標,要把恰恰帶給巴巴,發現這些人群給他的路上添堵。火車站——絕大多數來阿杰梅爾的朝圣者,必須通過這個門戶往返——已經被摩肩擦踵的旅客堵塞。顯而易見,根本不可能帶恰恰進入車站,或乘上任何赴孟買的列車。于是拜度雇了一輛出租車,把恰恰哄上車,駛往西南約30英里外的貝阿沃爾。
在貝阿沃爾,他設法讓恰恰上了火車,在多個聯軌站多次換車,他攜帶著這位珍寶,越來越接近巴巴。每當他要把恰恰從一部列車換到另一部,會要來專用椅子,那是各重要車站都備有,用于運送病弱人士的。他會扶恰恰坐上椅子,推到另一部列車。6月3日二人抵達薩塔拉,巴巴對恰恰的日常聯系就此開始。
想象一個長方形的小房間,四壁刷白,涼爽的灰色沙哈巴德石地板,兩扇窗,一道門直通房子后面,與低矮的廚房之間,那一片灑滿陽光的砂石空地。房間前面,用竹席圍屏隔成一小塊封閉區,面積和房間本身差不多,形成一個有點私密的院子,使房間保持隱蔽,不受那些在埃舍來回走動做各種事務的人打擾。
在這個樸素房間的一隅,恰恰坐在一塊長條席子上。他逗留薩塔拉的五周,始終沒有離開過這個房間。盡管白天大部分時間,他坐在習慣的角落,面朝門口,偶爾會自發地挪動幾碼,坐到房間的對面角落。
每天,巴巴用大部分時間,力勸恰恰喝茶進食,或者與他靜坐。這幾周期間,巴巴與阿里·夏,尤其與恰恰,靜坐一兩個小時后,出來時面色蒼白疲憊,衣服往往被汗濕透。似乎他與這些偉大瑪司特一起靜坐時,必須利用身體之透鏡,以聚焦他的無限能力之光線——故身體感受到壓力。
有一天發生一件趣事,說明恰恰過的那種反射式肉身生活。那天上午,巴巴一直給他茶,恰恰突然開始要更多茶,并把茶遞給巴巴,叫他喝。連續喝了十多杯,之后巴巴覺得很難再喝下。于是每次恰恰讓他再取茶,巴巴就拿著杯碟到門外,過一會兒重新進屋,把空杯碟小心地遞給恰恰,仿佛盛滿茶。接著恰恰會做出,把茶由杯倒入碟的動作——印度常見的飲茶方式——然后把茶碟,他顯然相信倒滿了茶,遞給巴巴。巴巴會做出喝茶的動作。這幕滑稽劇演了五十來遍,恰恰對此顯然并不知曉。
在薩塔拉,他不僅拒絕洗澡,而且過了幾周,才肯讓人脫掉他的臟破衣服。這位偉大的瑪居卜,在一間臟亂不堪的棚屋里,幾乎一動不動地坐了近二十年,盡管無視基本的衛生準則,卻依然有著強健的體格,這真是了不起。
在薩塔拉期間,恰恰不大喜歡說話,基本整天坐著,雙腿要么相當笨拙地折疊著,要么膝蓋靠近胸口,單肘或雙肘擱在大腿或膝上。他的頭部通常略前傾,故蓄須的下巴幾近抵著胸口,大多數時間,他的頭會略微上下擺動,好像列車上的打盹者。他的眼睛通常半開著,正如老年人常見的,角膜邊緣有一圈模糊的乳白色環。他的臉和頭較長,下方身軀(對帕坦人而言)卻不同尋常地小,面部表情好像一個人正做著奇異而可愛的夢——眼睛卻開著。那張大的半身照,體現出這種神情,有一種溫和單純。他說話簡練,音節模糊不清,像一個說夢話的人,說的話很少超出";Ao, ao(來,來)";、";Jao, jao(去,去)";、";Cha, cha(茶,茶)";或者";Nahin, nahin(不,不)";。
關于他的骯臟,關于他的拒絕洗澡,還有關于他的不愿穿干凈衣服,也不讓人給他的鋪蓋和周圍保持清潔,已經說得夠多了。很顯然,他意識不到身體功能,有著新生兒一般的滿不在乎;但與幼兒不同的是,他既不在意喂沒喂他,也不在意睡眠,也不在意身體的冷暖干濕;可盡管如此,他體格非常健康。
7月首周結束,巴巴解釋說,他對恰恰的工作已完成。7月10日,派拜度將他送回阿杰梅爾。
拜度講述,當列車駛入阿杰梅爾車站時,恰恰突然變得喜氣洋洋,自動地下車,快步走過站臺,出站后,立即坐入馬車。拜度上車坐他身邊,欣慰地發現如此省事,二人遂前往恰恰的棚屋。
然而現在,恰恰的心情似乎變了,他們抵達棚屋時,他卻坐在馬車后座,對請他下車充耳不聞。馬車夫耐著性子,等了近半小時后,抱怨說他該給馬喂食喂水了,便解下馬具,把車體連軸一起擱在地上。可恰恰依舊別扭地高高坐在后座,于是拜度抓住車軸,輕緩地抬起,故按重力法則,恰恰被倒出座位。
阿杰梅爾的民眾欣喜地看見,他們的恰恰又回到他們中間,因為一般人不曉得他是被帶到薩塔拉去見巴巴。拜度被告知,當地有個金匠十分敬愛恰恰,在恰恰離開期間,此人每晚來到他的棚屋,坐在那兒流淚。
就這樣,這位偉大的瑪居卜重返阿杰梅爾。個人覺得,他與巴巴之間的聯結將會時不時更新,巴巴要么會再度召見他,要么會再度去訪問他,正如之前他常做的,親臨克瓦伽·薩赫伯的圣陵附近那間奇特骯臟的棚屋。
最后,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夏姆司-埃-塔卜睿茲的詩句,雖然按字面上,該詩適用于瑪司特,但我認為,我們可以視之為適合這位偉大的瑪居卜。
(原波斯文略)
“屬神者是廢墟中珍寶。”
譯自威廉·鄧肯著《行道者——美赫巴巴與神醉者》第二章(The Wayfarers-Meher Baba with The God-Intoxicated by William Donkin, 1948)
- 簡介
- 每月活動記錄
- 美赫巴巴是誰?
- 怎樣憶念美赫巴巴
- 美赫巴巴答問
- 阿瓦塔的名
- 生平往事
- 美赫巴巴的父母
- 至愛的至愛
- 神圣的戀愛
- 美赫巴巴生平簡介
- 童年與青少年時代
- 面紗是怎樣揭開的
- 老家水井
- 生平四個階段
- 五位至師
- 赫茲拉·巴巴簡
- 納拉延·馬哈拉吉
- 塔俱丁巴巴
- 舍地的賽巴巴
- 烏帕斯尼·馬哈拉吉
- 阿瓦塔
- 阿瓦塔
- 圈子
- 阿瓦塔的圈子
- 當代阿瓦塔的訊息
- 美赫巴巴的睡眠
- 阿瓦塔作為第一個大師
- 阿瓦塔與賽古魯
- 彼得的否認與猶大的背叛
- 七月十日沉默日
- 阿瓦塔的獨特性
- 真正偉大
- 復活節
- 阿瓦塔的受難
- 顯現
- 門徒的寫作過程
- 原始問題的聲音
- 阿瓦塔的聲音
- 最偉大的顯現
- 阿瓦塔的工作
- 宇宙工作三階段
- 宇宙性推進
- 梵天之夜
- 神的工作不是說教
- 七月十日沉默日(重復章節)
- 信心與期待
- 兩則寓言
- 內在體驗階段
- 阿瓦塔的蒙辱
- 他的最后訊息
- 工作
- 蘇非教再定向指導憲章
- 宇宙工作
- 美赫巴巴與蘇非教再定向
- 美婼美赫【作者:戴維·芬斯特】
- 《美婼美赫》序言
- 1特別的孩子
- 2 學生時代
- 3 皇家旅館
- 4 白馬
- 5 托迪瓦拉路
- 6 默文吉
- 7 婚禮安排
- 8 美婼的決定
- 9 新朋友
- 10 戒指與照片
- 11 反對
- 12 美拉巴德
- 13 奎達
- 14 日出之歌
- 15 巴巴的勤務兵
- 16 考驗時期
- 17 沉默
- 18 拉妲
- 19 伊朗尼上校
- 20 修愛院
- 21 托卡的拔河比賽
- 22 鴿屋
- 23 去西方
- 24 神圣戲劇
- 25 瑪妮
- 26 西方人來訪
- 27 上美拉巴德
- 28 他不在時的忙碌時光
- 29 美拉巴德動物園
- 30 血誓
- 31 邁索爾摩耶
- 32 三環馬戲團
- 33 西方人在山上
- 34 船上閉關
- 35 里維埃拉河上的擠奶女
- 36 帝王臨朝
- 37 歸航
- 38 新來者
- 39 盤奇伽尼假期
- 40 白塔高聳
- 41 搖籃曲中道晚安
- 42 藍車旅行
- 43 在路上
- 44 瑣碎的爭執
- 45 球場屋
- 46 十勝節游行
- 47 戰爭工作
- 48 家門口
- 49 命令
- 50 戰時閉關
- 美婼美赫附錄一
- 新生活
- 新生活方案說明
- 美赫巴巴的新生活
- 什么是新生活?
- 新生活的意義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行乞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權威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危機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巴巴知道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情緒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特殊窮人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身份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美婼回憶
- 《新生活的故事》瑪妮回憶
- 培訓階段
- 末那乃息
- 完美者
- 自然——阿瓦塔的標記
- 金錢——完美的經濟學家
- 完人
- 完美的標記
- 辨喜論靈性導師
- 行道者【作者:威廉·鄧肯】
- 序言
- 關于瑪司特【作者:美赫巴巴】
- 瑪司特對人類的功用
- 靈性高級靈魂
- 靈性高級靈魂及瑪司特類型
- 五個最愛之說明
- 穆罕默德
- 恰提巴巴
- 卡瑞姆巴巴
- 阿里·夏
- 恰恰
- 瘋人埃舍
- 七個瑪司特埃舍之說明
- 阿杰梅爾
- 賈巴爾普爾
- 班加羅爾
- 美拉巴德
- 蘭契
- 馬哈巴里什沃
- 薩塔拉
- 那些見證者
- 美赫巴巴的瑪司特之旅
- 旅行示意圖、地名及數據
- 附錄說明
- 附錄(一)
- 附錄(二)
- 附錄(三)
- 附錄(四)
- 附錄(五)
- 補充附錄
- 最新消息
- 增補
- 再增補(一)
- 再增補(二)
- 再增補(三)
- 再增補:聯系匯總
- 作者簡介及后記
- 達善時刻【作者:美赫巴巴】
- 意義與體驗
- 真達善
- 真正生活
- 誠實
- 時間
- 唯一障礙
- 只要愛
- 真答案
- 救治良藥
- 雙重角色
- 愛的禮物
- 自我性質
- 緊抓衣邊
- 無限珍寶
- 完全忠于我
- 神圣戲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