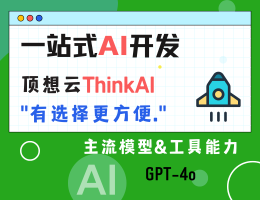作者:埃斯潘迪亞.維薩里
美赫巴巴在阿美納伽附近創建免費學校(直到英語七年級)那年,我16歲,在亞茲德(Yezd)上學。我母親的叔父拜度先生來我們家,想帶我去那所學校上學。我父親不想讓我離開。但我母親很想讓我去,就說服父親同意了。因此我跟拜度先生一起去美赫巴巴的學校。
我們六月份乘船啟程,快到卡拉奇時,海上刮起大風暴。我暈船厲害,嘔吐不止,醫生不得不給我注射了兩針。但病情仍不見輕,直到半夜好不容易睡著。我夢見了巴巴,醒來時精神爽快。健康地到了孟買。我們又跟拜度坐火車到阿美納伽,隨后到美拉巴德。
從亞茲德來巴巴學校的共有14個學生。早晨七點到達。拜度按身高給我們排隊。個頭矮的在前面,我個子最高,排在末尾。巴巴來了,拍拍每個人的頭。但他一走近我,卻轉過身,根本不注意我。我很難過——自問為什么巴巴不像對待其他人那樣也拍拍我。連續多日,心里總有一大塊郁結。
課堂上阿夫瑟瑞先生給我們讀密意詩。一天讀到薩迪的《薔薇園》(Gulistan?of?Saadi),說人將到達一個只看見神的地方。我問他是真的嗎?人能到達一個只有神的地方嗎?他回答說是的,并接著讀薩迪的其它詩。從那個時刻起,我失去了自然狀態。不能讀也不能寫。
就這樣幾天過去了,最后校長告訴巴巴說我一點也不專心學習。我不停地念神名。不知道自己在哪兒,也注意不到任何人或任何事。我覺知不到自己在學校,其他人坐在我周圍學習,直到突然看見阿夫瑟瑞先生站起來。我一轉過頭,就看見巴巴站在我身后。我站了起來。
巴巴打手勢問,“你為什么不學習?”
我答:“我學不進去。”
他問:“你想回你父親那兒嗎?”
我說不想。
他問:“想回你母親那兒嗎?”
我說不想。
“去你親戚家?你叔父家?”?他接著問:“是怎么回事兒?你不能學習出于什么原因?為什么不學習?”
我對他說:“我想走向神,知道神。”
巴巴說,“好吧,如果那是你真正想要的,我將給予你。但你必須服從我,按我的話做。”我等的就是這句話。因為我早已決定逃入森林,在那里尋求上帝,向神祈禱,不顧衣食或其它。巴巴是這樣安撫我的——他將把我想要的一切給我,向我展示神,條件是我必須聽從他,服從他。我說,“好。我準備好服從您。我保證服從您。”
就在那一刻,巴巴拉著我的手,把我帶進他的房間。他讓我坐在那兒,同時他自己躺在床上,蓋上被單,大約有20分鐘。隨后他起床,叫人送來一輛車子——如今你們在巴巴的博物館可以看到那輛人力車。巴巴會坐在里面,由兩個人拉著他在修愛院轉悠。他們先沿著馬路,再過鐵路,上山去美赫修道學校。巴巴上車,要我坐在他身邊。車上沒空位,我就站在巴巴右邊。出發前,巴巴要我抓住他的胳臂。我抓住他的雙臂,由兩個人把我們拉到山頂上的美赫修道學校。
巴巴說,“下來吧。”我下了車。
巴巴說,“你看見路有多顛簸,多可怕嗎?你要是沒有抓住我的胳膊,就會掉下車。同樣道理,你想行走靈性道路時,也必須徹底服從大師。”
我說,“好的,巴巴。”
于是巴巴告訴我,“從今天起,你必須保持靜默。從今天起,我就是你的上帝,我就是你的圣人,我還是你的先知。我是你的父母親;也是你的全部世間財產。你必須把一切都交給我,必須只專注我。絕不能注意其它事情,必須專注我。”
在那一刻我接受了這些。巴巴上了車,把我留在那兒。
當然,美赫修道學校還有其他孩子,但我沉浸于自己的狀態。第二天,我等待巴巴來學校時,遠遠看見巴巴的車,突然我的心中完全自發地涌起真愛體驗——我們必須對神的那種愛。從那時起,我知道了真愛的意義是什么,盡管很初級。巴巴走上山,對我說,“你若脫口說了話,應立刻讓人陪你下山找我,跟我坐半小時左右。”很多次,我忘了保持靜默,話脫口而出。每次總會有人陪我下山找巴巴。在那里我跟巴巴說話,巴巴總是說,“我饒恕你。”就這樣過了一斷時間,直到完全明朗——我的目標僅僅是巴巴。我開始意識到,我的一切都是巴巴,巴巴是神的化身。我親證了那一點。不像小巴巴那樣的高級狀態,但我從內心最深處真正地愛巴巴。
然而,逐漸地,我落入顛簸的思想之路。這些念頭讓我迷失了道路和方向。巴巴完全清楚所發生的一切,總是問我在想什么。對我說,“你應該把這些胡思亂想從腦子里扔出去。你非常幸運。應該對我全神貫注,為我放棄一切;無論發生什么,都交給我,始終把注意力集中于我。”我才16歲,只是個孩子,做不到。我努力把念頭和想象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,想有什么念頭就有什么。不過,這些障礙開始出現在我的念頭里,最后到了讓我恨巴巴的地步。
每次見巴巴走來,我都會逃離,不愿讓巴巴看見我。巴巴也改變路線,迎面朝對我走來。就這樣繼續著。我感到不該有那些對巴巴的念頭,想那些有辱于他的可怕念頭——尤其是當我想到巴巴是偉人,不是常人,想到我在他的學校,吃他的飯食的時候。我決心違背巴巴,讓他從學校開除我。我會到世間一段時間,也許會失去這些念頭,然后就能再回來,繼續走直道。
因此我違背了巴巴。拜度先生去告訴巴巴此事。巴巴問我是否想回家,去孟買或亞茲單。我說,“是。我想離開。”他便令拜度為我打點好行李,之后帶我去孟買,把我交給叔父,拿到收條再回巴巴這兒。不到十分鐘拜度就收拾好了,過來對巴巴說一切準備妥當。巴巴說,“好吧,帶他離開。”我開始站立,但雙腿卻動彈不得,下半身癱瘓,直至腰部。我用指甲按大腿,卻毫無知覺。腰部以上沒問題,我能夠感受,看和說,卻走不了一步。巴巴打手勢要我站起來,但我卻不能。于是他打手勢要拜度把我帶過來。拜度像拎小鳥
似的將我拎起,把我帶到巴巴跟前。(那時巴巴在一間屋子里閉關六個月,每天只喝一杯牛奶和也許一杯熱水。六個月后閉關結束時他不能走路。經過鍛煉走路才恢復正常。我當時就坐在那兒,所以記得這個。)。巴巴把手放在我脖子上。我坐在他面前。他問,“你為何不走?不想走?”我說,“不想。我不想走。”又說,“我曾想離開,但現在不想了。”巴巴打手勢說,“你擁有愛。”接著,突然擁抱了我。就在他擁抱的那一刻,我的腿開始恢復生機。我能走路了。
要我留下是巴巴的愿望。這就是為什么他讓我的腿失去生命。那是巴巴對我的持續恩典,我永遠難忘。每次看見我,巴巴總是說,“想我,愛我,想我。”他叫我不斷地專注他,想他,不想其它。盡管如此,這些念頭和想象障礙仍舊打擾我,我尚未達到對它們的控制。終于有一天巴巴叫我過去。他在二號廳,現在的博物館。我進去后,巴巴叫我坐下。有半小時的時間,問我都想些什么,要我把這些念頭告訴他。但我羞于說出口——因為我不斷地想一些侮辱他的壞念頭。我不告訴他——我害羞。直到最后,巴巴親自對我說,你在想這些這些事情。但我還是不讓他知道,假裝不明白他在說什么。我希望地面裂開縫,當場把我吞進去。意識到巴巴知道我的每一個念頭,我感到極其低卑羞恥。就連這個念頭,巴巴也在字母板上寫出。我還是不告訴他,假裝不明白。這時巴巴打手勢說我對此一清二楚,只是假裝不明白。他對我說,“我從未對任何人等過這么久,來告訴我什么東西。你真有好運,運氣真好。你很幸運。為什么要將這一切拋棄呢?”說完就走了。
我在那個顛簸路上呆了一些時間,但逐漸地開始對那些念頭略加控制。從巴巴說出我的念頭那一刻起,我便開始逐漸地控制自己的思想。以至到后來,只要我一坐下想巴巴,其它念頭就進不了腦子。那時我的念頭完全處于我的控制之下。坐下靜心時,腦子里沒有其它念頭。就像一個人坐在坦克里,打過來的子彈全都落在地上。我會感到念頭想進來,卻進不來,不能進來坐在我腦子里。有時候我靜心時,巴巴會走過來。每次巴巴從屋外走來,我都能感覺到他來了。隨著這樣的感受,我會發現巴巴在我旁邊。他會把我的頭攬在他胸前;因為我在靜心,巴巴會把我的頭抱在自己胸前,過一會兒才離開。
完全專注于靜心時,我會感到自身有一種極其精微輕柔的光。并專注沉浸于此。之后我會睡不著,那時我沒有睡眠。處于一種精微的醒覺狀態。我所經歷的喜悅和奇妙感受如此強烈,我可以肯定地說,假如這發生在正常人身上,他們會震驚得心臟猝發,精神崩潰。因為他們是沒有能力承受的。我在這種狀態期間,巴巴時而會問我,“你感覺如何?在發生什么?”我剛開口,他就說,“好了。其余的別說了。”我便閉口不言。
有時候巴巴會在晚上來到二號廳,坐在石子地上。他就這么坐著,孩子們都圍聚在他身邊。我會走過去,挨著他坐下,雙膝剛好碰到他的膝蓋。我只是想坐在那兒,消失在巴巴里面,消失在那個感受里。無論何時和巴巴坐在一起,或在別處,我整個生命都充滿對巴巴的渴望和愛。絲毫感覺不到自身的存在——不是通常的我是誰,在做什么?我內里只有巴巴的愛。在某個程度上,這種微妙的渴望,這種靈性渴望,是在我的心靈里,難以言表。無論何時從遠處看見巴巴,他都會雙唇做個親吻姿勢,走過來,拍拍我的頭。那時我會感到精微的靈魂,完全感到自己的精微靈魂,如同香精和玫瑰水。似乎我的靈魂被那個香精玫瑰水洗滌。隨著巴巴把手放在我頭上,往下按,好像他是在清洗我的靈魂,直入深底。這讓我陶醉于那個狀態,無法用文字表述。當然那種陶醉是靈性陶醉,跟酒醉不同。完全不同。它極其微妙,極其愉悅,極有創造性,如同天堂之風,拂面吹來。我無法描述那個天堂來風的感受,或那個精妙的音樂。在那里時,這種感受一直不斷,我持續地體驗著。(之后這種體驗繼續著。當然現在我在更高級的層面上體驗它。不再跟那時一樣。)
有一天巴巴叫我去他那兒時,我正處于這個狀態。突然之間,我自忖,可能巴巴要送我回家——伊朗的亞茲德。到了巴巴那里,他剛要告訴我,我就意識到他要說的話確實如我所想。他說,“無論我對你說什么,你都要服從。”我別無它擇。不能說不。只好說,“是。”巴巴說,“好,你不得不回伊朗,直到我再叫你回來。無論何時我叫你來,你就可以回來。”這讓我無比難過悲傷,以至于當時所思想和感受的全部思想和狀態都被離別的悲哀所籠罩。巴巴命令我回伊朗時,我的悲哀如之前的幸福喜悅一樣強烈。我對自己的靈性工作無法多想。不知道該做什么。就像個瘋子。我不能做自己的靈性工作,與之失去了聯系。
最后我服從巴巴,啟程回伊朗。回到伊朗后,我逐漸地意識到,我仍然擁有跟巴巴在一起時,我所看見并感受的一切感受和事物。所以我繼續進行靈性工作。自從跟巴巴同坐人力車后,我從遠處看見巴巴,他讓我體驗到神愛,直到今天,我還沒有完成這個體驗。那次經歷向我表明,我該怎樣愛上至愛,該怎樣愛至愛。那時只要巴巴一個眼神,那個體驗就是我的。它尚未結束,我還沒有完全體驗巴巴曾一度向我示現的那個。
田心譯自《拉姆玖日記1922-1929》蘇非教再定向出版社1979年出版,第549-555頁。本文是1975年歐文·拉克和法哈德·夏法醫生在伊朗德黑蘭采訪埃斯潘迪亞.維薩里時的錄音
- 《美婼》
- 《美婼》序言
- 第一章 最初的一瞥
- 第二章 童年
- 第三章 等待巴巴召喚
- 第四章 第一批女子
- 第五章 在郵局的日子
- 第六章 修愛院年間
- 第七章 納西科
- 第八章 美拉巴德山
- 第九章 總是在遷移(上)
- 第九章 總是在遷移(中)
- 第九章 總是在遷移(下)
- 第十章 新生活
- 第十一章 訪問西方
- 第十二章 德拉敦
- 第十三章 美拉扎德
- 第十四章 永遠在一起
- 曾經如斯【作者:埃瑞奇】
- 你們都聽我說過
- 這件事
- 這件事兒發生在
- 蒙辱與榮耀
- 美赫巴巴時常提
- 神秘學沒有位置
- 他們罵我時,卻在想念我
- 克里希納·奈爾的故事
- 薩洽·莽的故事
- 獨處
- 漿果
- 規則
- 德希穆克
- 愛因斯坦
- 金德
- 古斯塔吉
- 健康
- 不可能
- 基泊爾·辛
- 金錢
- 帕瓦蒂伽
- 巴巴被捕
- 直接回家去
- 無私服務
- 睡眠
- 不可測量
- 美赫巴巴是誰?
- 策略
- 污染海洋
- 要求愛
- 靜心
- 跟隨巴巴旅行
- 古魯帕薩德事件
- 拜度
- 我們應該怎么做?
- 痛苦
- 拋錨在世間
- 巴巴大笑
- 幫助他人
- 業相
- 親密
- 黑伽亞
- 珠寶商與騙子
- 天堂里的宮殿
- 早年
- 秘密
- 憤怒
- 檀香山邂逅
- 取悅巴巴
- 辟爾法如·夏
- 美與丑
- 阿亞茲
- 奎師那瑪司特
- 度內
- 嘉爾·科羅瓦拉
- 機智
- 新生活
- 祈禱文
- 愛池
- 丟失在他的海洋里
- 誠實
- 摩耶
- 克里希納·奈爾
- 是那樣嗎?
- 該怎么做?
- 石板
- 神兄【作者:瑪妮】
- 放風箏
- 莫后拉
- 被遺忘的玩具
- 牛眼糖
- 上帝的小衣服
- 媽母與爸伯
- 他的蓮足
- 圣克魯斯記憶
- 小王冠與便鞋
- 愿您知曉
- 幸運的鴨子
- 漫漫歸家路
- 惟有巴巴是
- 愿望實現
- 還有一年
- 水牛
- 樹屋
- 真正的修女
- 沉默未破
- 最好的朋友
- 來自海洋的邀請
- 上帝的衣櫥
- 神人剪影【作者:伊麗莎白·帕特森】
- 多年前的今天
- 首訪澳大利亞(一)
- 首訪澳大利亞(二)
- 不管你是否跟隨我
- 神秘地精確
- 愛之湖
- 承諾
- 神圣游戲【作者:庫瑪】
- 上帝先生
- 不是善人是神人
- 千萬替我保密
- “我把她搬走!”
- 你必須先走第一步
- 迪娜的故事
- 瑜伽師
- 鞋子與花環
- 尋找,你將被找到
- 什么都不要,你將得到一切!
- 誰是圈子成員?
- 大英帝國的死亡令
- 好的壞的都是我的
- 門徒回憶
- 開始的時候(上)
- 開始的時候(下)
- 《神曰》的寫作
- 在石頭上播種
- 受辱–因禍得福
- 緯露與薩若希
- 讓愛成為唯一的祈求
- 第一次達善
- 大師是怎樣工作的
- 美赫巴巴看電影
- 打井與信心
- 特殊的大師
- 母親與女兒
- 愛給巴巴戴花環
- 巴巴與科學家
- 上帝會照看結果
- 服從之禮物
- 當他接管時
- 問題是怎樣解決的
- “你難道不信任我?”
- “讓我永遠伴隨你”
- 愛的呼喚不可思議
- 受苦的另一面
- 在神人身邊長大
- 愛之舞【作者:瑪格麗特·克拉思科】
- 第一個命令
- 幽默的一課
- 第一次跳舞奇遇
- 你永遠贏不了
- 巴黎與馬賽
- 違令—梅瑞迪施
- 一個離開巴巴的人
- 第一次印度之行
- 王后,紅衣主教與郡主
- 戲劇方面的事情
- 第二次跳舞奇遇
- 愛麗絲·索·菲舍
- 鬼魂
- 暗夜
- 鏡子
- 圖表
- 昆廷
- 與神共舞
- 納西科的故事
- 在困難條件下訪問
- 向他臣服【作者:羅妲·阿狄·杜巴希】
- 前言
- 第一章
- 第二章
- 第三章
- 第四章
- 第五章
- 第六章
- 夢見至愛【作者:瑪妮·伊朗尼】
- 閉關山的燈火
- 修道院地震
- 夢見至愛1
- 神圣門衛
- 美婼減輕我的負擔
- 上帝的朝廷
- 無雙的隊伍
- 雌鹿也做過
- 上帝的衣櫥1
- “我愛你,我的姐妹”
- 娜芙蒂蒂
- 他們在哪兒?
- 呼拉圈
- 發大水
- 巴巴,請別叫醒我
- 勝利的呼聲
- 我的金魚朋友
- 樹洞
- 最后一個訊息
- 巴巴簡關店
- 沉默
- 我的永恒時刻
- 為王后跳舞
- 看不見的禮物
- 真正的珍寶【作者:魯斯特姆·法拉提】
- 祈禱的秘密
- 神圣意志
- 佯裝生氣
- 通過恨來記住
- 婚姻
- 唯有念記重要
- 生活的熱忱
- 靈性健康
- 儀式教規
- 純潔的愛
- 莫忘目標
- 懷著感情念記
- 美赫巴巴之道
- 羯磨與恩典
- 巴巴獨自做工作
- 說真話講策略
- 控制頭腦
- 靈性訓練
- 和諧
- 死亡
- 化工廠之戰
- 巴巴形體的重要性
- 犧牲
- 神愛
- 經濟大師
- 危機即機會
- 神圣淹沒
- 減速器故事
- 強過你的痛苦
- 無限珍寶
- 和寶吉捉迷藏
- 成與敗
- 消滅自我
- 只依賴巴巴
- 平衡業相
- 三類生活
- 自由與奴役
- 蹈火
- 邀請他的恩典
- 想象實在
- 劍師
- 《真正珍寶》第2輯
- 不斷憶念的禮物
- 巴巴知道什么最好
- 真英雄
- 神圣意志與自由意志
- 成為他的
- 這會把你引向神
- 膽敢要巴巴
- 邀巴巴參與你的弱點
- 放下小事
- 幻相勢力
- 放下執著
- 燃燒的心
- 做出努力
- 猴心
- 心靈這般
- 心會長大
- 真正謙卑
- 巴巴要什么
- 超越對錯
- 血之淚
- 只是服從他
- 沖出幻相
- 神醉
- 巴巴說話時
- 怎樣祈禱
- 生發渴望
- 神名的力量
- 神名能轉化
- 《真正珍寶第3輯》
- 真正珍寶的寫作
- 續書的創作
- 美婼的關愛
- 巴巴救了我
- 懶惰的愛者
- 腦心和諧
- 用憶念戰勝嗔恨
- 持續自如的憶念
- 正確的選擇
- 永遠的伴侶
- 真正的祝福
- 真正的恩典
- 準備的程度
- 生發創造“在”
- 重要的是憶念
- 幸運的瘋人
- 假古魯與垃圾桶
- 完人的作為
- 全能的上帝
- 失去的機會
- 完全的交托
- 碾磨過程
- 重要的是取悅他
- 無上真理
- 巴巴的沉默
- 背叛引向神
- 只要放開手
- 公義與仁慈
- 唯一的守諾者
- 當簾幕拉開
- 蔻詩德最后的日子
- 真愛史詩
- 分離之痛
- 藝術與神在
- 讓頭腦安靜
- 祈禱的力量
- 堅定的信心
- 巴巴為世界受難
- 巴巴的禮物
- 應盡的責任
- 事實與真理
- 滿德里讀心靈
- 一切來自巴巴
- 罩著面紗的神
- 非常體驗
- 榮耀主的工具
- 神的禮物【作者:阿娜瓦絲】
- 前言!
- 第一章-
- 第二章-
- 第三章-
- 第四章-
- 第五章-
- 第六章-
- 第七章
- 第八章-
- 第九章-
- 第十章
- 第十一章
- 第十二章
- 第十三章
- 第十四章
- 第十五章
- 第十六章
- 第十七章
- 第十八章
- 第二十章
- 第二十一章
- 第二十二章
- 第二十三章
- 第二十四章
- 第二十五章
- 他給予海洋【作者:娜玖·考特沃】
- 前言-
- 父親夢想成真
- 美拉巴德山上的生活
- 巴巴,我們的大爹
- 他的陪伴甘露
- 服從的教訓
- 接受他的意愿
- 守夜—父親的不可能任務
- 我的西方巴巴家庭
- 惟有您是我的神
- 神永不死
- 美婼與至愛團聚
- 內在力量之禮物
- 后記 畢生的撒晤斯
- 努力與恩典【作者:達文·肖】
- 努力與恩典 序言
- 第1章 神圣至愛
- 第2章 美赫巴巴的工程
- 第3章 大師幫助
- 第4章 面紗制造機
- 第5章 溶化面紗
- 第6章 凈化心靈
- 第7章 改變價值
- 第8章 改變焦點
- 第9章 交出一切
- 第10章 表現方式
- 第11章 改變范式
- 第12章 保持靈性流動
- 第13章 殲滅虛妄
- 第14章 重新編程
- 第15章 消除煩惱
- 恩典的雨露
- 他也是可憐的羅亞斯德!
- 巴巴腳前的一束花
- 有幽默色彩的秘密禮物
- 超出了理解的慈悲
- 關心、寬恕與慈悲
- 巴巴的捉迷藏游戲
- 全知遍在的至古者
- “一定是瘋了!”
- 在巴巴的愛里無憂無慮
- “在某個時間,某個地點,以某種方式!”
- 重溫耶穌的臨在
- 認出卻又忽視
- 在他的看不見的手中
- 跳起比根舞
- 一個夢與兩只鞋
- 活出眾生一體真理【作者:克雷格·伊恩·拉夫】
- 愛的見證
- 關于穆罕默德瑪司特
- 努力見到我的本來面目
- “做我的活花環”
- “你怎么這么久才來?”
- 全知者美赫巴巴
- “我是愛之洋”
- 神奇的達善
- 革命者成為巴巴愛者
- 巴巴回應了我的祈禱
- 到至愛足前的旅程
- 他給予愛的擁抱
- 一個無神論者的神愛證明
- 蔻詩德的內視
- 用歌聲榮耀主
- 與神的約會
- 遇見美赫巴巴
- 紅心之王
- 收獲他的恩典
- 首次見美赫巴巴
- 愛——心靈的語言
- 巴巴的全知
- 白血球
- 臣服于美赫巴巴
- 平衡與凈化
- 阿瓦塔式巧合
- 輝光
- 娜迪亞·沃琳絲卡的靈性轉化
- 確立對巴巴的愛
- 美赫免費診所
- 美赫學校
- 馬杜蘇丹的故事
- 交談
- 不為什么
- 同喚醒者交談
- 回到中心
- 自我痼疾
- 放大權威
- 滿德里
- 埃瑞奇
- 阿迪
- 帕椎
- 普利得
- 滿德里為何受苦?
- 女門徒的角色
- 寶加入巴巴的故事
- 弟弟佳爾的故事
- 美婼-美赫,美婼-美赫
- 佳露和谷露【作者:嘉娜克】
- 佳露和谷露(1)
- 佳露和谷露(2)
- 佳露和谷露(3)
- 佳露和谷露(4)
- 愛者故事
- 毛拉巴巴之墓
- 在瑞什可什遙見閉關山
- 比利的故事
- 瑜伽,瑜伽師和圣人
- 弟子準備好
- 誰是巴巴愛者?
- 巴巴寇斯若
- 教導的時刻
- 巴巴幫我們改掉惡習
- 戰爭結束了
- 孰能無過
- 埃斯潘迪亞
- 比夫的故事:神圣時機
- 唐娜林的巴巴故事
- 心懷巴巴離世
- 在印度遇見奇異博士
- 保羅·柯瑪的故事
- 從佛陀到美赫巴巴
- 巴巴在中國
- 美赫巴巴訪問上海和南京
- 《語錄》的翻譯與其他
- 美拉巴德日記(一)
- 美拉巴德日記(二)
- 美拉巴德日記(三)
- 巴巴生日快樂!(1894年2月25日)
- 給美婼美赫的詩
- 美拉巴德日記(四)
- 美拉巴德日記(五)
- 美拉巴德日記(六)
- 美拉巴德日記(七)
- 愛者眼睛里的至愛
- 永恒者
- 三摩地的守護者
- “阿瓦塔之寓”之旅
- 巴巴紀念日之旅點滴
- 羅珊
- 美赫就是神
- 巴巴,生日快樂。
- 讀書摘錄
- 朝圣路上的心得
- 阿瓦塔的酒店
- 回憶印度的人和事
- 朝圣分享
- 朝圣隨筆
- admin的美赫巴巴朝圣之旅
- 朝圣初旅
- 朝圣者之聲
- 愛的朝圣
- 愛的朝聖
- 美赫文問答錄
- 海瑟講故事
- 安醫生的故事
- 美赫納施講故事
- 朝圣感觸
- 關于神名“呼”
- 一百零一個神名
- 20年后,我找到了夢中故地
- 為什么過去我一直不敢說自己是美赫巴巴的弟子
- 朝圣美赫巴巴三摩地之后
- 高速路上的生死日志
- 相信,就會看見(上)
- 相信,就會看見(中)
- 相信,就會看見(下)
- 相信,就會看見(后記)
- 靈性工作者的任務
- 靈性工作者的任務-
- 為自身靈性自由而工作
- 為人類靈性自由而工作
- 靈性認識導向靈性自由
- 怎樣通過直覺服務
- 怎樣通過靈性認識服務
- 通過靈性認識明智地服務